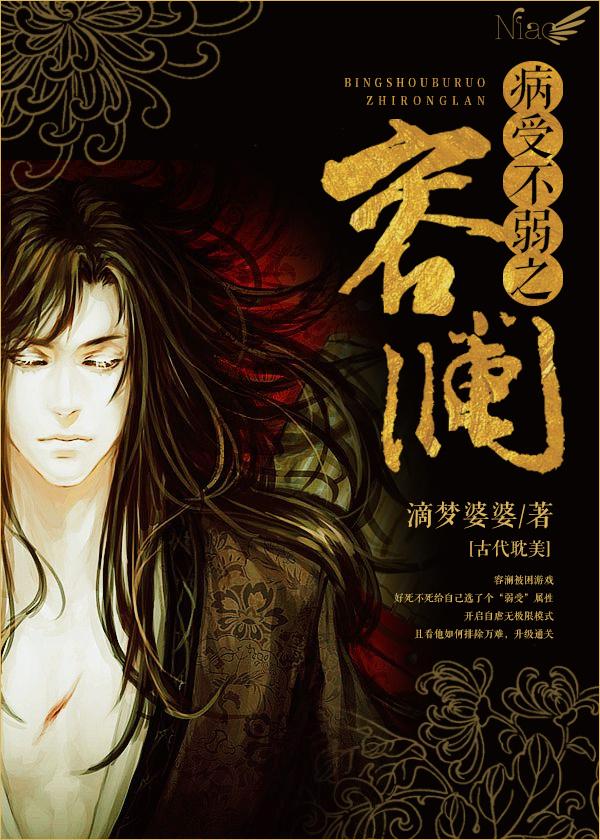</script>容澜一觉醒来已在去往苗南的路上。
身下马车驾得很稳,几乎没有晃动,他睁眼轻声唤身侧的人:“大哥,我睡了多久?”
“小澜,你醒了?”见到容澜醒来,容烜紧绷的神情终于放松,“你睡得不久,不过半天时间。”
容澜冲他微微一笑:“哥,让你担心了!”这笑容虚弱苍白,连续两次心疾发作,对容澜的身体是不小的负担。
容烜心疼抚弄弟弟的额发,温柔问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容澜抿抿嘴摇头:“没有不舒服,有些渴。”
容烜赶忙倒了水,扶容澜起身,却见小澜对自己讨好一笑:“哥,你喂我吧!”手臂似乎睡觉的时候被压住、有些发麻,手也虚软无力,但更重要的是,此刻容澜想要对着容烜“撒娇”。
容澜破天荒主动要求容烜喂,容烜微愣,随即将弟弟搂抱在怀前,仿若哄孩子一般宠爱道:“好,大哥喂你,来,慢点喝。”
这一刻,容烜心底异样甜蜜,小澜的坚强隐忍只让他心碎,他喜欢小澜这样依赖他。
容澜窝在容烜坚实的臂弯里,由着容烜喂自己,乖顺得像只小猫咪。
他没想到,不过说了点玩游戏时陈芝麻烂谷子的糟心事来拒绝重翼,会搞得那般身心俱疲……
从议政殿一路走出皇宫,他吞了整整一瓶护心丸,才勉强撑着没有倒下。是以,在宫门外见到容烜时,他是真的觉得自己见到了世间唯一可以全身心依赖的亲人。
容澜想着,不禁重复一遍当时的话:“大哥,你在真好!”
容澜这突如其来的动情“表白”令容烜心头猛颤,他俯身在容澜发间不着痕迹落下一吻:“小澜,大哥会永远都在!”
马车忽然慢了一下,车门被人推开,“烜大哥,王……”
弥儿端着托盘低头走进马车,一抬眼瞬间惊呼出声:“啊!王兄你醒了?!”
容澜吓了一跳,面色越发白,不待他答话,紧跟弥儿身后,王褚风提着药箱也走进来,“弥儿公主还请不要惊咋言语,你王兄心脉薄弱,受不得惊吓。”
“哦!”弥儿认真点头,轻手轻脚把托盘放在车内矮几上,用气音对冷着脸的容烜道:“烜大哥……王兄的药……”
容澜暗自扶额,多年未见,弥儿这丫头还是和以前一样……蠢萌。只是,以容烜对弥儿的不待见,弥儿能求得容烜同意她一路随行也着实不容易。
容烜喂弟弟喝药,王褚风拿出脉枕给容澜把脉。
对于王褚风的出现,容澜心知肚明是重翼的安排,但容烜都没有拒绝重翼好意,他就更没有必要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他心口堵的厉害。
王褚风把脉后道:“脉象时急时缓,此乃心有郁结,目前症状不算严重,你要注意不可多思多虑!”
心有郁结?!容烜手中喂药的汤匙一抖,离开重翼,小澜果然是伤心至极的,或许自己不该反对小澜与重翼在一起……
容澜倒是平静点头:“我知道了,等苗南的事了结,我便什么也不再想。”
只有完成那个未完的千秋约定,他和重翼之间才算真的两讫。
皇宫之中。
墨玄不解:“主子,您真就这样放容公子走了吗?”明明千辛万苦才找回来。
重翼垂眼,再看一遍千羽辰送来的书信:“离魂蛊蛊王需要蛊阵才能解,放澜儿去苗南是唯一的办法。”
有容烜的尽心照顾,外加王褚风的精湛医术,容澜身体很快大好。
而有弥儿的存在,去往苗南的旅途总也不会无趣。
“弥儿,王兄我想听曲子了,你来弹一首!”
“是!王兄!王兄想听什么?”
“随便。”
“弥儿没听过《随便》这首曲子,是王兄自己谱的吗?”
“……”
“弥儿,王兄许久不听你背诗,来背一首!”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你怎么不问我想听什么了?”
“王兄日日发呆思春,一定想听这首!”
“……”
可惜,旅途没能一直这么无忧无虑下去。
容澜好几次睡醒后手臂发麻,而且麻木持续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
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次数多了才察觉出不对。他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离宫前一日,他心疾发作在敏学殿陷入昏睡,醒来后手麻得几乎不能动,便抱怨重翼握他手握太紧。
可他以往昏睡无数次,哪次醒来手不是被人紧紧握着?但哪次也没出现手被握麻、不能动的情况。
所以,根本就不是由于外力作用,而是……
……
“离魂蛊寄居在宿者心内……中蛊者一开始会时感周身乏力,时间长了便会丧失行为能力,如同没有魂魄之人只能躺在床上等待死亡!”
……
容澜回忆千羽辰对离魂蛊的解释,后脊阵阵发凉。
再联想之前千羽辰欲言又止地劝他早些去苗南,如今想来,就连重翼会放他走也透着几分古怪。
容澜什么也没问容烜,只是对容烜道:“大哥,我的身体已经好了,我们骑马早点到苗南吧。”
对于小澜的请求,容烜从来只有妥协与溺爱。
抵达苗南的前一日,投宿客栈落脚之后,容澜支走容烜,如常要弥儿弹琴给自己听。
弥儿跪坐古琴前:“王兄想听什么曲子?”
容澜却是一改往常“随便”二字,点了曲名:“就弹广桴子为佛尔谱的那首《余生》吧。”
弥儿听到这曲名愣了半晌,悠扬琴音响起。
容澜一手托腮,侧身歪在软榻上瞧弥儿弹琴,不得不说,弥儿长得很合他眼缘,圆脸圆眼,弯弯的眉毛,笑起来还有两个煞是可爱的酒窝,可惜……
……
“用你的血给我解蛊,你会怎么样?”
“弥儿的命是王兄救得,当初如果不是王兄心软,弥儿早死在从苗南来京城的路上……”
……
容澜收回思绪,眸光微沉,翻身下榻,坐到弥儿身侧,“想不想听王兄为你弹一次?”
王兄会弹琴?!弥儿惊讶得嘴巴大张,却依旧谨记不能对王兄大声说话,起身让出古琴,轻声道:“想。”
就见容澜双手抚上琴弦,修长白皙的手指在琴弦上拨动,幽远曲调便自指尖流出,弹的正是方才弥儿所奏《余生》。
这是容澜唯一会弹的一首曲子。
曲入高\潮,琴音豁达宽广,带了对人世余生无限期许,弥儿痴痴听着,却是不禁落泪。
《余生》是历史上著名琴曲大家广桴子为其久病不愈的友人佛尔所谱赠曲,以激励朋友积极坦然地面对疾病、余生自会希望无穷,相传,佛尔听此曲后不久便奇迹般病愈。
可王兄的病……
不!王兄的病也会好的!
“啪”!
琴音戛然而止!
断弦划出一道血线。
“啊!王兄!你流血了!”弥儿回神,忘了不能大声说话,惊叫着捧住容澜被琴弦划破的手指,“王兄!疼不疼?”
容澜脸色煞白望向自己的手,许久轻声道:“不疼……”
弥儿眼眶蓄泪,心刚刚放下,就听容澜补充道:“我的手已经没什么知觉……”
啪嗒!啪嗒!眼泪从眼眶掉落。
“不会的!不会有这么快!”弥儿慌张掐上容澜的手,几乎掐出血来,可容澜却连眉毛都没有抬一下。
竟是真的没了知觉……
弥儿哭着凝望容澜清瘦苍白的双手,王兄的手如此漂亮,骨节分明、手指匀称修长,不该再也无法写字、弹琴!
不该是这样的!
容澜本是碰运气,但弥儿的反应足以说明她是知情者,于是冷声问道:“你们究竟瞒了我什么?”
弥儿闻言猛一抽泣,愣愣抬眼,“王兄……?”
容澜语气更冷:“是要我彻底变成废人才肯说吗?”
“不会的!蛊王一定能解的!王兄不会变成废人!”弥儿脱口而出。
逼得想要的答案,容澜抽出一块丝帕递给弥儿,缓和语气道:“蛊王是怎么回事,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弥儿接过丝帕自己给自己擦眼泪,擦了一半,嘴巴大张指着容澜:“王、王兄,你的手还能动?!”
“本来就还能动。”容澜的右手早已半残废,骗过弥儿这个傻白甜自是简单得很。
弥儿后知后觉自己上了当,然而悔时晚矣,该说的、不该说的,她都已经说了,只得老老实实交待一遍蛊王的来龙去脉。
“也就是说,你的血根本解不了我中的离魂蛊,至多只能让我像废人一样在床上躺一辈子,苟延残喘留条性命,对吗?”
弥儿点头,眼睛已经哭成兔子。
“咳!咳!咳——!”容澜俯身咳出几口血,再抬眼时眼底一片冰寒:“你可以走了!我不会放过你母亲和哥哥!你也没必要再留下用命替他们赎罪。”
“王、王兄……?”弥儿被容澜此刻的模样吓住,眼前男人面白如鬼,唇染鲜血,就像地狱的勾魂使者,她害怕地往后躲,逃也似得奔出房门。
容澜冷眼瞧着面前一架断弦琴上的血,掏出药瓶把瓶中药丸悉数倒进嘴里。
心脏的疼痛慢慢减弱。
这副残破不堪的身体他早就厌烦,折腾到现在,他不能娶妻生子,至多活不过四十,而且随时可能因为心脏病猝死,居然还是有人不遗余力地想要害他。
他不计较,不想恨谁,不代表他是任人宰割、毫无反手之力的病秧子!
要让他生不如死,那便看看,最后痛不欲生的究竟是谁!
容澜勾唇冷笑,笑容透着凄楚,然而染血的红唇却无端带了邪魅森冷,瑰丽得有些可怕。
在进入苗南的前一夜,弥儿这位苗南公主失踪了。
翌日,容烜带着容澜回到容家在苗南的祖宅。
两人走在长廊上,容澜忽然生出物是人非之感,想起当年自己在这里上蹿下跳地求着容申给他家法受,要攒够一张免关卡。
他停下脚步,望向身侧如今唯一还在的亲人,“大哥,以后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容烜心头猛跳:“小澜,你好端端说什么胡话?!”
容澜搂住容烜:“我总是会比大哥先走,这不是胡话,是愿望。还有,我想自己完成跟重翼的约定,不管我做什么,都请大哥不要阻拦。”
容烜永远无法拒绝弟弟的请求,哪怕一次次眼看弟弟受伤,他回抱容澜,感觉心在流血:“好!大哥答应你!”
每一次小澜为了重翼的江山殚精竭虑,都惹得满身伤痕,小澜已经再承受不起任何伤害,他却依旧无法拒绝。
容烜没想到,这次的妥协几乎就是与弟弟的永别。
那染血的祭坛是他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噩梦。
“墨玄,带我去见慕绍澜。”
墨玄奉命押送慕绍澜来苗南交予容澜,容澜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吓了一跳,“容公子身体不适吗?脸色这么差?”
容澜笑着反问:“你何时见我脸色好过?”
墨玄皱眉:“主子说,暗卫在苗南皆听你调遣,人就关在里面,你想如何处置也都由你。”
容澜走进暗牢,低头打量被关押之人,这是他第一次与传说中的弟弟见面。
慕绍澜抬眼,却不是第一次见哥哥。
他手脚被铁链拷着,形容狼狈,却是目光狠厉,言语狠毒:“瞧哥哥面色白得像鬼一样,还真是难看!容烜怎么会爱上你这种要死的病……”
慕绍澜骂得起兴,容澜却是没有任何兴趣听他说话,捏开他的嘴巴把手中一瓶液体灌进他嘴里。
慕绍澜感觉下颌剧痛,恶心的浓汁就流进口中,他想挣扎,竟是挣脱不开。
捏在他下颌的手格外苍白,肌肤几乎透明,根根青色血管清晰可见,修长的手指像是注了内力,他没想到,容澜看起来病入膏肓,会有这么大力气!
瓷瓶见底,容澜松手,慕绍澜俯身剧烈咳嗽:“咳咳咳!你给我喝的什么?!”
容澜轻声吐出三个字:“蚀心水。”
慕绍澜脸色骤变!“你——”
却见容澜转身:“我不喜欢别人和我长得一样,把他的脸给我毁了!”
“是,公子!”
“啊——!”
墨玄带容澜走出暗牢,听见身后传来慕绍澜凄厉的惨叫,不由侧头望向容澜:“你恨他?”
容澜瞥一眼墨玄,表情冷淡:“恨?我唯一怨恨过的只有你主子。”
墨玄皱眉,觉得自己开启了一个非常不友好的话题。
就听容澜又道:“是为了替你主子免除后患,省得日后慕绍澜再生个什么儿子出来,又要演一次复国的戏码。”
墨玄心下了然,“你母亲我也按照你信中要求一并带来了。”
容澜点头:“我正好有事问她。”
容府,乌梓云被引进前厅,见到立在自己面前的人时,有些愣神。
容澜道:“母亲是认不出儿子的真假吗?”
乌梓云面色一瞬惨白:“我会竭尽所能为你寻得解蛊之法,这是我欠你的。”
容澜沉声:“令牌的真假可以看不出,刚出生的儿子也可以认不清,但贴身服侍多年的婢女突然换了人,母亲难道从未起过疑心?”
乌梓云脸色更白。
容澜不等她回话,轻笑道:“母妃不必再为别人的儿子忙碌了,早些准备回宫吧,毕竟母妃才是父王的正妻。”
乌梓云望着身前面容苍白的年轻人,面上黑纱渐渐被泪水打湿,“容有波澜,‘澜’这个字是将军起的。”
容澜道:“父亲不会白死。”
乌梓云点头转身,“好,我知道了。”
接下来的日子,容澜不是向容烜询问苗南朝局,就是命墨玄搜集苗南民情。
千羽辰将重蝶探得的消息告知重翼,户部批文下来后准备离京时,突然接到飞鸽传书。
“少庄主,不好了!太长公主落入苗南太妃的陷阱,被抓了!”
乌溪云察觉重蝶偷听到自己与影一的对话,便故意透露蛊阵,引重蝶去乌家老宅查探,又提前布下陷阱,将她抓获。
一个公主的作用堪比十万大军,何况还是大周皇帝同母同胞的亲妹妹,不得不说,乌溪云这招先手出得快、准、狠!
“驾!驾!”千羽辰带人一路快马赶去苗南。
如不尽快救出重蝶,一旦乌溪云利用重蝶要挟大周,便只能交出南王慕绍澜这个筹码作交换,如此,局势会对容澜大大不利。
然而千羽辰还没到苗南,就传出失踪已久的南王重新回宫的消息。
一月时间,足够澜公子当日在议政殿拒婚之事传到苗南,掀起惊天波澜。
慕绍澜一回宫就借机向族人宣控:自己的哥哥恋慕大周皇帝,要将苗南拱手送上,是苗南的叛徒,人人得而诛之!
一时,苗南上至朝臣下至平民都对容澜恨之入骨。
容澜却是挑在此时高调入宫,在慕绍澜归朝的庆贺晚宴上拿着南王令牌道:“持令牌者才是南王。”
满朝文武对着两位长得一模一样的王,根本傻傻分不清究竟谁是谁。
只见乌溪云一把揭掉儿子的面具,慕绍澜被送回来时毁了脸,她正好为儿子修回原本的面容。
“先王殉国前,仅留了本夫人在身侧,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先王临终传位于哀家肚里的孩子,哀家有先王王谕为凭,各位卿家若有不信尽可一览!”
乌溪云语毕,影一闪身将一道王谕奉上。
满殿朝臣一片哗然!南王与澜公子竟不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南王并非王妃所出,而是溪夫人的儿子?!
乌溪云自登太妃,便从未保留身份,她经营二十几年,苗南复国后有一半朝臣实际听命于她,她更是趁着容烜离开军营这段日子,夺了容烜兵权,如今她才是苗南真正的掌控者,南王令牌算什么?此刻王谕在手,即便非她掌控的新臣,也不得不屈从于众。
满殿朝臣与苗南旧族皆向着慕绍澜跪拜:“大王!”
慕绍澜扬笑望着容澜:“如何,哥哥?看在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我留你这个叛徒全尸!”
正在容澜寡不敌众之时,大殿上突然传来女子沉冷威严的声音:“还不快将苗南的叛徒给哀家抓起来!”
苗宫禁卫顷刻冲进殿中,乌梓云黑纱遮面走在最前,指的人竟是容澜。
乌溪云一愣,禁卫怎么会听命于乌梓云?而且乌梓云为何要抓亲生儿子?!就见一向不与人争的姐姐走到她面前,目光冷冽中隐隐带着报复的快感:“很意外吗?溪云妹妹!你以为你养的是自己的儿子吗?”
乌溪云被这目光看得后脊一凉:“乌梓云,你什么意思?!”
乌梓云道:“若不是如今真相揭穿,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当年我的另一个儿子一出生便死了!彼时你将绍澜抱给将军,两个刚出生的孩子长得颇为相似,但明显容澜的身体更弱小一些,我疼他体弱,便将两个孩子偷偷换了,想着容府小公子的生活总是好过奴仆。溪云妹妹,你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吧?你害死将军,这就是你的报应!”
满殿众人听得云里雾里,乌溪云却是忽然疯了一样指着乌梓云道:“这不可能!你骗我!你骗我!”
乌梓云扬笑:“你若不信,那便滴血验亲如何?来人,拿两只碗来!”
“是!太妃!”
两只白玉碗,其中放了清水,若为亲生母子,血液自会相溶。
乌溪云急切得将自己的血滴在碗中。
容澜冷眼瞧着,轻轻撩起衣袖,将手腕缠绕的白纱揭下,白纱染血,那纤细的手腕上新伤叠着旧伤,不知多少道口子。
两位太妃皆是看得心惊。
自从察觉手臂发麻的蛊发症状,容澜便日日割腕放血,还魂丹无法终止蛊王的活动,唯有失血才能令蛊王入眠。
滴!
鲜血滴入碗中,化成浅浅的粉红色,又很快聚拢起来,与乌溪云的血溶成一片!
乌溪云的心几乎瞬间崩溃!她可以不爱儿子,但她怎么可以……赢不过乌梓云!!
所有人震惊!如果澜公子才是溪夫人的儿子,那么南王之位自是澜公子的!更何况他手中还握有南王令牌!
容澜早在朝臣中安派了自己的人手,等的就是这刻!
几人忽然向着容澜跪拜:“参见大王!”
再然后,便是所有朝臣以及世族大家跪拜:“参见大王!”
容烜杀了禁卫统领,也走入大殿,跪在容澜身前:“参见大王!”
谁是最终的赢家,不言而喻!苗宫此刻已全权在容澜掌控!
容烜一出现,慕绍澜就目光狠毒望向容澜:“你夺走了容烜不算!你连我的母亲,我的地位都不放过!我要杀了你!”
不等容烜出手保护弟弟,影一已将慕绍澜拦下,护在容澜身前:“不得对南王无礼!”
慕绍澜没了武功,手脚筋脉被挑断,根本不是影一对手,踉跄一步跌倒在地上,这一刻,便是他人生绝望的开始,比得不到容烜更绝望!
他趴在那里,抬眼痴痴望向影一,这个只为听命于南王之命而活的男人,再也不属于他……
……
“阿元!”
……
他忽然无比想念影一第一次叫他“阿元”这个名字的场景,那一日春风拂面,他在树下练剑扭伤了脚,影一从天而降,他那时想的是,这个大哥哥是神仙吗?
慕绍澜失去一切,望向自己所谓的生母,却发现乌梓云也跪在哥哥脚前,高呼着:“参见大王!”
而将他养大的“母亲”已然神智时常。
容澜平静接受着满殿跪拜,扬声道:“本王不日即将举行祭祖仪式,感召祖先,携我苗南子民归顺大周!”
南王即将祭祖,主动归附大周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而之前痛恨澜公子是苗南叛徒的民众皆等着看他被祖先抛弃。
祭祖开始这一日,以童子之血验过王族印记之后,南王手捧令牌跪于祭坛正中。
祭祖为血祭,首先要跪上三天三夜感召祖先,若所请之事祖先应允,跪请后血祭,祭坛会开出血图腾,若不允,祭坛则无任何变化。
第三日,苗都几乎所有臣民都聚集在祭坛四周,苗南祭祖的仪式异常神圣!而南王令牌之所以是王的象征,正是因为那令牌为开启祭坛的钥匙!
只见南王将由两枚铁令组成的令牌拆开插入坛眼,然后割腕将血源源不断淋在令牌之上。
一瞬间,血色在坛上石纹飞速蔓延,就像盛开的图腾花,数万民众惊呼!
归顺大周得到了祖先应允?!
只听南王道:“周朝皇帝仁德广施,前二十年,我苗南得其荫护,风调雨顺;近三年,复国后灾祸不断!是以祖先为我苗南后世之福应允本王所请!尔等还不与本王一同跪谢祖先!跪拜周朝!”
南王一席话令这两年备受战争摧残的苗南百姓记起曾经归顺大周的安逸日子,皇帝确实仁德广施,这份“仁德”竟是已然感动了苗人先祖吗?
不断有人开始跪拜!
“谢先祖启示!”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谢先祖启示!”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容澜听着耳边震天高呼勾起嘴角,缓缓闭眼,这千秋的约定他终于完成,可实在太累了……
他的心已经跳不动了……
世间渐渐陷入黑暗。
“小澜——!!”
容澜甚至不曾听见容烜穿透万人高呼的惊喊!
他只记得祭祖前,乌溪云那疯子一样的咆哮。
“离魂蛊的蛊王根本无解!无解!!”
“啊!你们别再逼我了!!别再逼我了!”
“我是故意说给重蝶听得!!就是要骗你们不杀我!!”
“他是我儿子!!!我会不想救他吗?!”
“老天!你为什么要对我乌溪云这么残忍?!!啊——!”
所以,该死的人,终究都生不如死!
残忍吗?
这一场爱恨情仇根本没有人赢。
……
“母妃,在水里放入白矾,我与你自此不再是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