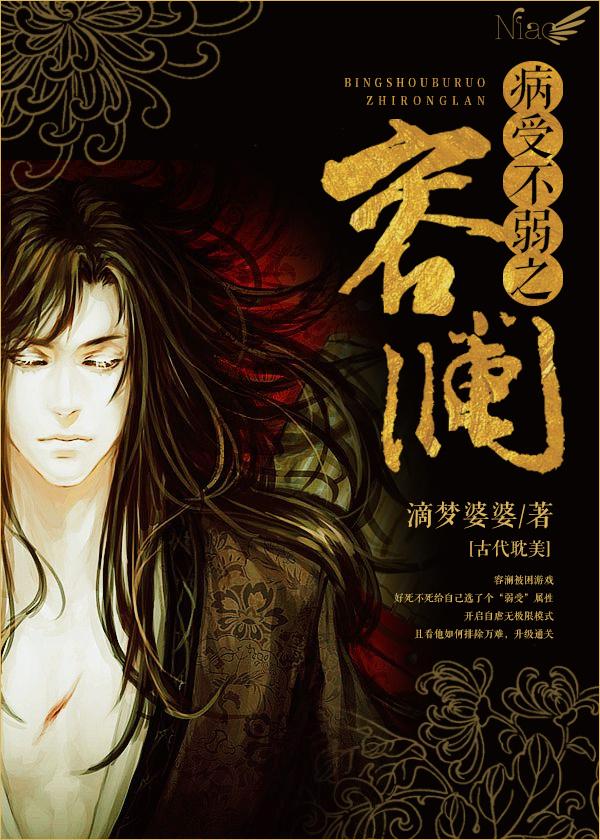……
“太子殿下,皇后娘娘根本没有串通北厥、谋反叛乱!”
“当年北厥对大周开战,是因传出皇上要为容尚书废后的传言,皇上为保容尚书,用太子殿下的安危逼迫娘娘,娘娘为了太子您才自请废后、认罪伏法!”
“娘娘是被皇上和容尚书一起冤死的!太子殿下一定要为娘娘报仇啊!奴婢身为娘娘的贴身宫娥,没有陪娘娘一起死,忍辱偷生苟活至今,就是为了寻得时机告诉太子真相。”
“北厥的使团就要进京为皇上贺辰,奴婢所言是真是假,太子殿下自可以去问使团中单于亥斛曾经的亲随!”
……
“是你害死我母后!”
一道闪电划破天际!
轰隆隆!
噼噼啪啪的雨点坠下,前一刻还月明星朗,转眼一如当年洪州一夜,夜雨惊雷。
那人早已经死了……
为什么还活着?!
“啊!快来人呐!澜大人落水啦!”
“快来救人呐!”
宫娥惊呼声响彻雨夜。
重翼闻讯赶到时。
满池荷花在疾风骤雨中飘零,池中无数灯火摇曳,人头攒动,寻喊声此起彼伏。
“澜大人!”
“澜大人!”
禁军统领马翌跪身:“启禀皇上,禁……”
“噗通”!
重翼根本不听马翌禀报,已然跳入池中。
“皇上?!”马翌紧随皇帝跳下水。
“皇上,您的伤还不能沾水啊!皇上!您快上岸吧!”张德不会浮水,只能在池边焦急跟着皇帝的身影来回跑。
重翼在水中疯了一般找人,然而劳无所获,道道闪电映上他惨白的脸,他的雨幕中大喊:“澜儿!你在哪儿?!你回答我啊!澜儿——!”
……
“……只要你保证小澜不再受任何伤害……”
……
他为什么要留澜儿独自在荷花池边?!
他明明发誓要保护澜儿再不受伤!
胸口一剑诛心,绝望与悔恨带着勾刺,在心底一点一点撕扯蔓延!
又是一道闪电!
轰隆隆!远处突然有人应着雷声高喊。
“找到了!”
“找到了!”
“澜大人找到了!”
重翼在绝望中乍然回头,就见雨幕中,一名禁军高举一团白物往岸边游。
不是澜儿……?!
容澜适时走到荷花池,撑着一柄伞,墨发如瀑垂散在身后,一笼白衣只有衣角被水浸湿,走到那禁军身边,接过自己的宠物,眉目淡淡训斥小狐狸:“叫你乱跑,这么多人找你!”
重翼望向那岸上的人,呆了一瞬,跃出水面就紧紧抱住容澜:“澜儿,你没事?!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你……”
“这次送你一只活的做分手礼物!”容澜打断重翼,将湿漉漉又可怜兮兮的小狐狸塞进他怀中,“你以后冲它发情,正好是公狐狸,符合你的性取向。”
容澜说完挣开重翼,撑伞走远。
重翼抱着“烧”而复得的新分手礼物愣在雨里。
就听容澜远远扬声道:“啊,对了!它今天刚有名字,叫’澜大人’!”
重翼彻底石化。
所谓“澜大人”,竟是太子太傅给自己宠物起得名儿!
禁军听见宫娥呼喊赶来救人,却见大雨中,太子太傅从水中露头,指着一池荷花道:“慌什么?不过是我养的雪狐跳进池塘不见了!它的名字叫澜大人。”
“……您快去换身干爽的衣物,这里有小的们寻!”
皇宫禁军早接到圣旨,若遇急情,万事以保护太子太傅安危为要,这么大的雨,池水寒凉,马翌和手下哪里敢让容澜自己寻?
重翼这一番心急如焚、痛苦绝望,从头至尾都像是容澜为了发泄心中不满故意折腾他的乌龙。
而这世上,敢如此“玩弄”重翼这个皇帝,还让皇帝没脾气的,大约只有容澜一人。
闹剧落幕,人声远去。
躲在假山后的重文低头看向自己的手。
那一年洪州城一夜大雨,电闪雷鸣,他闯进父皇的房间,房间的床上躺着一具宛若活人的尸体。
指尖至今残留着那人面颊冰凉细腻的触感,可那人分明没有呼吸,已经死了。
……
“太子殿下想不想看看你的太子太傅究竟是谁?”
“太子应该已经知道先皇后是怎么死的,难道不想为自己的母后报仇?”
“只要太子按我说的做,就可以让那个人永远消失!”
……
洪州一夜发现的秘密让重文莫名坚信,没有人能够超越容尚书在父皇心中的地位,太子太傅烧了那只草偶,获罪的却是惠嫔,于是他心生猜疑,抱着小狐狸悄悄跟来荷花池,见到了面具下的另一张脸。
漫天大雨冲刷,轰轰雷鸣不绝于耳,重文蜷缩在假山后的小小一隅角落,感觉外面整个世界都翻天覆地,不是他原来认识的样子。
一柄纸伞忽然遮住了他身前风雨,然后一只手将他抱起,他趴上一人肩头。
那人的怀抱并不温暖,带着丝丝凉意,清瘦而且单薄。
待反应抱自己的人是谁,重文僵硬的身体忽然开始急剧颤抖,狠狠咬在那人肩上:“是你害死我母后!”
活着血水,重文却只尝得到自己口中咸咸的泪:“为什么是你害死我母后?!为什么要是你?!”
“为师犯的错,不会为自己辩解,废后确实是为师向你父皇所求,只事情的真相远不是太子殿下知道的那样,逝者已矣,皇后娘娘是否真的背叛大周、为亲兄亥斛谋求虎口关内为师不予评说,但有一点,你必须相信你的父皇,他是爱你的。皇后娘娘临终,也一定这样告诉过太子殿下。”
重文瑟缩的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皇后临终的话萦绕在他耳畔。
……
“文儿,母后是大周的罪人!你舅舅妄图称霸中原,发动战争,母后助纣为虐,如今大周边关血流成河,百姓流离失所,母后犯下的错就由文儿来替母后赎罪可好?”
“文儿,要记住母后的话,大周是你未来的天下,你要变得勇敢而强大,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你的子民!”
“文儿,母后要走了,你不要怨恨你的父皇,这一切都是母后咎由自取。你父皇是爱你的,他答应了母后会好好教导你,你要听你父皇的话,他是这世上最好的皇帝……”
……
“文儿,母后要走了,你不要怨恨你的父皇……”
“你父皇是爱你的……”
“不要怨恨你的父皇……”
“你父皇是爱你的……”
重文一遍遍回忆,口中咬得更狠,他分不清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他宁愿相信母亲的话,但他不能怨恨父皇,他该怨恨谁呢?
如果没有这个人,一切是不是都不一样……
为什么这个人要再出现,要让他像父皇那般喜欢上他,对不起母后?!
他应该恨这个人吧?
如果一定有所谓阴谋,如果一定要替母后报仇,那他就该恨这个人!
重文咬在容澜肩头,在一片血的腥甜中渐渐哭着睡着。
从荷花池到太子东宫,容澜一手撑伞,一手抱他,走得很慢,也很吃力。
容澜想,如果再选择一次,自己会直接用免关卡跳过“废后”的任务,利索地脱光衣服躺在重翼身下,与自己选的主角攻“共度*”。
他这一生很少后悔,但这件事,他是真的后悔了,并不是因为执着“废后”让他丢了性命、被困在这个时空,仅仅因为他拆散了一个家庭,令一个无辜的孩子失去母亲。
天下可怜人多得是,他恻隐不过来,然而他想要有一个幸福的家,想要自己的孩子有幸福的家,却是亲手毁了别人的家,此为世间最难逃的良心债!
亥姝是咎由自取不错,亥姝的死也不是他直接导致,但他实不该推波助澜,搅进这一滩浑水,到如今无法逃脱。
没有他,重翼不会逼死亥姝,他心知肚明。
入夜一场雷雨下得快,去得也快。
走回太子东宫时,雨势已渐渐停歇。
“太子殿下回来了!”
“啊!殿下受伤了吗?身上这么多血?!”
容澜将重文交给太子宫的宫人,示意近旁宫女不要吵闹:“太子没有受伤,是睡着了。太子淋了雨,你们去九重殿请名太医来看看,别生了风寒。”
“是,澜大人!”宫人们赶紧都去忙着照顾太子,也没甚人再去关注那些血究竟从哪里来,风寒非同小可,自古多少皇子都早夭在此,若是太子有个三长两短,他们都没命活。
晚膳后,太子殿下自从见过皇帝与惠嫔便独自出了东宫,不让任何人跟着,眼看夜幕降临突然一场夏季的雷雨,太子出宫时没有跟着,宫人们慌张去寻,这被太子太傅抱了回来,果真是淋了雨。
容澜回到屋中自己给自己处理伤口,重文咬得他肩头血肉模糊,容澜咬牙用酒沾湿棉帕清洗,然后洒了金疮药,缠上绷带,换了件干净的衣服,转身又出了东宫,往宫门走。
刚才一场乌龙,重翼强行下水寻人,剑伤崩裂,失血过多,出了荷花池没走几步就昏了过去,皇帝伤情紧急,哪还有人顾得上他?
容澜折返荷花池,将重文送回太子东宫,会往宫门去,先是有太子指证草偶狐狸是他拿的,紧接着就有人推他下水、打算嫁祸太子,那封请柬他原不打算明着回应,与德妃的哥哥产生什么牵扯,如今看来,却是非应不可了!
虽然晚膳后一连串发生了许多事,但眼下时辰其实并不算晚,入夜时分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下过,天气凉爽,正是京城贵族寻欢作乐的好时候。
花街柳巷,灯红旖旎。
伶青馆门前,迎客的小官儿见有新客入馆赶忙迎上,瞬间失了魂一般呆在原地。
而下一刻,整座热闹非凡的伶青馆在陷入短暂沉寂后,一片抽气惊叹。
但见走进馆中的男子,芝兰玉树,皓齿明眸,莞尔一笑,倾三世众生倏忘今宵。
“那公子是谁?!”
“那公子长得好生俊美!”
“天下第一美的澜公子也不过他这般了吧!”
“听说京城近来有位貌比澜公子的神秘男人时常带儿子出游,莫非就是他?!”
伶青馆作为京城最大的一间男妓馆,汇集天下各式多才多艺的顶尖美男,而此刻台上弹琵琶的正是馆中头牌,濯莲君。碧池濯濯,清莲窈窕,人如其名的绝好颜色。然而濯莲君与这位公子相比,简直泥土比之白云,荧虫较之皓月,根本不值一提。
伶青馆不若胭脂阁,来这里的人大都痴好男色,自这位公子一出现就成为全场焦点,众人目光不再往台上看,只瞧他一人。
而他面对无数窥视目光似乎习以为常,行动间依旧落落大方,镇定自若,这就更显得他气质高洁,不染俗尘,越发令人神往,却又不敢再唐突冒犯。
曾楚阔低头望向楼下男子也不由惊艳,澜公子果真如传言里那般天人之姿,又叹,澜公子带太子出宫向来大张旗鼓、毫不遮掩,竟是反倒让世人猜不出他的身份,心智也绝非常人可比。
这边曾楚阔心中无限感慨,那边容澜已万众瞩目走进他所在的雅阁。
雅阁专门用来给京城中有头有脸的达官贵人们喝花酒议事,内外两扇窗,内可观馆中表演,外可赏一池碧湖,布置清新雅致,当然,雅阁里也设有床榻,万一两扇窗都不方便开,自然要排上用场。
“就是这一间了,公子请!”负责引路的小厮说着恭敬退下。
曾楚阔回神,离得近了重新打量容澜一番,不由又失神,他不好男风,但赏美之心人皆有之,面前男子五官均美得无可挑剔,但最美的还是一双眼,狭长的眼眸,眼尾微扬,瞳仁点漆一样黑亮,光华流转间,一个抬眸就摄人心魄。
曾楚阔想着深望容澜眼底,却是瞬间垂目,只感觉这双眼自己若是再望,恐怕就要失魂,他顺势起身,拱手作揖,不失礼节:“澜大人之名,果然百闻不如一见,曾某久仰!”
容澜拱手回礼,不见多少热络:“曾将军,有礼。”曾楚阔打量他,他也打量了对方一番,风头正盛的年青武将,眉宇硬挺,轮廓卓然,依稀与德妃有些兄妹像。
两人落座,美酒佳肴很快就上。
曾楚阔直奔主题:“今日约澜大人见面是想聊表谢意!澜大人在皇上面前为曾某请功封侯,曾某心中感激!”
容澜语气淡淡:“我不过是劝皇上论功行赏给太子殿下做个表率,最终还要皇上心念有功之臣,曾将军才得以封侯,将军该谢的人不是我。”
这话明面是礼貌谦逊,说白了意思就是,你要谢去谢皇上,跑来请我是请错了人。
曾楚阔面上敬意不减,叹道:“澜大人住在宫里,要约见一面着实不易,肯赏脸受曾某之邀,是曾某的荣幸!”
容澜摆手:“不是我肯赏脸,是曾将军盛情难却。”
曾楚阔自然听出澜公子这是不悦自己送请柬的方式,端起酒杯赔罪道:“曾某鲁莽,但实在感念澜大人恩情,此番回京又处处听闻太子太傅盛名,一时起了结交之心,澜大人莫怪!”
容澜不碰酒杯,直言拒绝:“我身体不好,无法饮酒。”
曾楚阔的注意一直都放在容澜脸上,隔着面具他自然看不出容澜脸色有什么不对,此刻经容澜这么一提醒,这才想起传言里澜公子体质孱弱,略一细心观察,眼前男子果然呼吸浅薄急促,再看那扶在桌案上的手,若不是指尖泛起一丝血色,当真可以用苍白来形容。
赶忙放下酒杯,改换茶杯:“是曾某大意!”
容澜却是也不碰茶杯,面色微沉:“不瞒将军,我今日会应邀前来,是有些话想告诫将军,说完便走。”
容澜说话并不客气,曾楚阔倒是好脾气,洗耳恭听的谦逊态度,笑着点头:“澜大人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容澜道:“德妃娘娘如何对付我,我倒是都不在意,但若她想动太子殿下,动手前,不妨先考虑考虑三皇子的安危。”
曾楚阔脸色骤变,“还请澜大人明示!”
容澜说得云淡风轻:“我已向太后娘娘请旨,所有皇子都将往太子东宫,跟在我身边学习。不知曾将军还要不要我说得再明白一点?”
曾楚阔后心一凉,澜公子这是直接拿了三皇子的性命做要挟,竟丝毫不在意鱼死网破?!若三皇子在他手上有什么意外,他也绝活不了。
看来妹妹要对付的人当真极不好惹。
却听容澜又道:“还有一事,惠嫔已被打入冷宫,如果德妃娘娘想去陪自己的好姐妹,我可以送她一程,算作回礼。”
曾楚阔满额冷汗:“澜大人今日告诫,曾某记下,相信德妃娘娘也会记下。”
容澜看出曾楚阔动摇,由强势改为循循善诱:“我为将军请功虽有着旁的目的,但也是真心敬重将军为大周驻守边南,希望将军功绩可以光耀门楣。再者,朝廷赏罚有度,才能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前来效力,皇上如今推行各项新政,正是求才若渴之际,曾将军年华正好,前途似锦,行事前也请三思,不要辜负当年季大将军对你的举荐之恩。”
曾楚阔听过容澜一席话,终于明白为何世人对澜公子颇多赞誉,更明白曾家别想撼动澜公子一根手指。
此人心智超然,摸得透每个人的软肋,妹妹的软肋是三皇子殿下,而他最不能辜负的人就是大将军季鹏贺,季将军当年不仅举荐他领兵苗南,更在战场上于他有活命之恩。
曾楚阔终是叹声:“曾某并不是贪恋权利之人,也会好生劝慰娘娘!”
“如此最好,告辞!”容澜感觉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不欲长久逗留,得了曾楚阔态度,便起身告辞。
容澜不愿与曾楚阔有过多牵扯,婉拒了曾楚阔的相送,自己走出雅阁。
伶青馆内众人目光依旧聚焦在他的身上,皇帝公然承认自己喜欢男人,这男妓馆竟也比以往风靡,这里汇集京城达官贵人,见过太子太傅的也不是没有,而明晨,就不知要有多少弹劾太子太傅逛风月场的奏折要被送到皇帝的御案上。
容澜想想,觉得自己现在就可以替伤情复发的重翼头疼。
然而容澜大约忘了,这世上最令重翼头疼的是他的身体。
容澜这一日短短个把时辰之内落水、淋雨又失血,更是没有按时往九重殿温泉接受施针,他能意识清醒走回太子东宫的居所已是奇迹。
这第二日,重翼养足精神醒来,不是被接连不断弹劾太子太傅的奏折惹得心烦,也根本来不及因了容澜瞒着自己当真去了伶青馆这种地放气恼,而是惊闻太子太傅病重,高烧不退、不停咳血,直接罢了早朝!
重翼跌跌撞撞闯进容澜房间时,重文就趴在容澜的床边,一双眼,眼底似有泪花,闪着意味不明的亮光,懦懦问他:“父皇,老师是不是就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