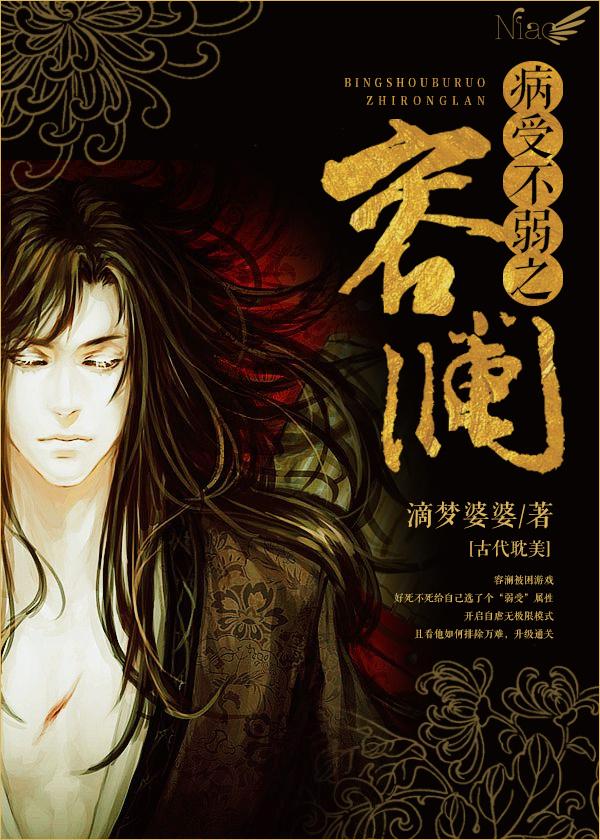重翼原不过就是问问容澜的意见,想听听多家之言,并没打算将这军队忧关的大事交给自己还未全全信任的人,见容澜推辞便不再坚持,只道:“夜深了,你也早点休息。后日就可回京,你离家许久,也盼望多时了吧。”
容澜跪在地上头晕耳鸣,隐约听出重翼是不打算为难他了,不由后悔,早知道这么容易,他就不跪了。他一边凭借毅志谢恩起身,一边觉得不该赌气,到头来难受的还是自个儿。
重翼大约还记得容澜体质不易行跪礼,不放心地叮嘱一句:“你若身体不适,便叫王褚风给你瞧瞧。”
容澜轻“哦”一声,转身走出屋子。屋外风雪刮在他脸上,让他发烫的面额觉得舒服不少,神智也清晰了一些。
他踩着棉花似得走过院子里的积雪,回到自己住的屋前,见重翼派给他的小公公殷勤迎来,张口便骂:“没事儿别来烦我!爷不待见你!”
他怒意未消地冷喝了一通心情稍微舒畅一些,却又忍不住骂自己古代游戏玩多了,竟也染上迁怒无辜、端架子搞封建的恶习。
进屋提了几本册子又走出来,缓和了语气交待解释一番:“把这个拿给李编纂,告诉他按照前面的方法算完就可以交差了。我太累,回京前只想睡觉,除非天皇老子驾临,否则谁来了都给我拦在外面,尤其是王太医!”
容澜说完回屋插门,合衣躺在床上。晕眩一阵阵袭来,他盯着帐幔缓缓闭眼,意识消散前在心中无奈轻叹,非得靠这种法子他才能好好睡个觉吗?
这游戏真的玩得他有些身心俱疲……
屋外,那小公公刚被莫名骂了,转眼又见容澜没事儿似得交待他差事,只感觉跟在皇上身边的人都是阴晴不定,惹不得的主儿,简直如奉天命一般遵照容澜的话行事。
王太医每日清晨例行看诊都被他想法子挡了回去。
结果临到回京启程的时辰,他在屋外叫了许久也不见屋里睡觉的人有起身的动静儿,想推门进去瞧瞧,发现门推不开。
他开始着急,想寻人撬门进去看看,一转头就见到容澜口中的“天皇老子”站在他身后,他吓得浑身一个哆嗦跪在重翼脚前:“奴…奴才,参见皇上!”
重翼皱眉:“你慌什么?”
张喜吱吱唔唔半晌,憋出一句话来:“容公子说他累!”
就这一句毫无逻辑的回答,重翼脑中“嗡”的一声,不知为何,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容澜出事了!
那屋门在重翼面前犹如无形,他破门而入,疾步走到床前:“容澜!容澜!”
“你慌什么?”
却没想到,屋里容澜正悠闲地坐在桌边喝水,见他冲进来,嘴角勾笑不急不慢将他方才的话重复一遍。
重翼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感觉被人狠狠玩儿了一遭,这种体验怎么说呢?像是天上掉下来一坨鸟屎,你着急推不开身旁的人,结果那屎却掉在你脑袋上,而你着急的人一脸无辜问你为什么不躲?
这是重翼活了二十八载从不曾经历过的感受。他紧张,庆幸,愤怒,又好笑,到最后只平静答道:“我慌你。”
这下,轮到容澜有些不自在,感慨能做皇帝的人果然不简单,什么情况都能处变不惊,都要不落下峰。跟这样的人玩,他还是太嫩,何况他的身体也玩不起。
他放下杯子,起身行了个揖礼:“皇上,容澜睡觉前特意吩咐过喜公公,如果是您传诏我一定就不睡了,您亲自来叫容澜起床,容澜惶恐。”
“惶恐?”重翼瞧着容澜一脸稀松平常的神态,觉得他向来都显病态苍白的脸今日竟还带了红润,冷笑道:“朕看你这一觉睡得不错,想来不该打搅你的。既然醒了就走吧,都等你一人了。”
容澜挪了两步,发觉自己勉强醒来撑到现在已是极限,却又不想重翼瞧出什么端倪,他自打不想要重翼心疼的眼泪之后,就是身体再难受也不愿人前示弱,他没有这种故意招人可怜的习惯,当然亲人面前除外。
“皇上,我想沿途看看风土民情,就不和你一道儿回京了吧。”
重翼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原地不动的容澜,似是在权衡什么,半晌道:“那便随你。大夫、小厮还有马车都给你留下,你一路注意安全。”
容澜眨眼,没想到重翼会这么体贴,还叮嘱他一路注意安全,扯出个笑脸:“那你也一路注意安全。”
重翼闻言警惕地瞧了容澜一眼,终是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
容澜目送重翼出了房门,就再站不住,顺着桌脚滑坐在地上。
“公子,您这是怎么了?!”张喜进来服侍,见状慌忙扶他床上躺下,焦急询问。
容澜摆手:“我有点热,地上凉快而已。别动不动就大惊小怪。”
他轻飘飘、软棉无力的教训显然没什么威慑力,张喜变得更加大惊小怪起来:“啊!公子!您身上怎么这么烫?!王太医!王太医!”
张喜隔着严冬厚衣竟仍能感受到容澜身上灼人的热气,王褚风匆匆走进屋子,只一眼就抱怨道:“容公子,您几时烧的,怎的不告诉老夫?还要这奴才阻挡老夫看诊?”他说着卷起容澜的衣袖,行针驱热。
容澜浑身无力,微阖眼睑,声音虚浮:“前天下午烧的,我睡一觉发发汗就好,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干嘛兴师动众告诉你。”
王太医气急:“发热乃是险症,拖延了是要人命的!”
“我这不是还活着吗…”容澜不耐,撑着口气拔了王褚风插在他胳膊上的针,“张喜,扶我上马车,我要回京。”
“啊?”张喜大张着嘴,愣愣问:“公子不是要游历山水吗?”
王褚风扶额:“寒冬腊月的游什么山水?你一个伺候人的奴才,真假话听不出来?”
容澜也哭笑不得,只是他此刻真的没有精力去嘲笑别人,伸手抓住床沿自己坐起来:“王太医,路上再给我瞧吧。”
王褚风皱眉:“容公子这身体…何事着急非要此时上路?你不是已经推脱了缘由,打算养病吗?”
容澜扶上张喜肩头:“快过年了,我想和家人一起,你们也别被我拖累,误了团圆。”
王褚风收了药箱,抬眼瞧着身前扶着一个小公公缓缓走远的年轻人,忽然觉得有点心疼,旁人不知,他身为这年轻人的主治大夫却是清楚万分,那一身的病痛折磨,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也不明白这么年少的孩子是凭借什么一个人熬住,竟还瞒天过海,装得全天下都以为他不过寻常体弱,甚至还能挑灯夜熬完成那么繁复的工作。
王褚风摇摇头,由衷觉得容澜如今还走得动路堪称医届奇迹!
容澜的马车一路行驶地并不慢,而且称得上快,原因无他,容澜病得不轻,所需珍奇药材非要在皇宫宝库才有得寻。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也有,只是千羽山庄比之京城更远,恐怕来不及。
容澜卧在车里的软塌上,头脑昏沉,却是醒着。自从心口开始隐隐发疼,他想要安安静静昏睡就成了奢望。
以前他觉得这是游戏,里面的一切都是假的,按照游戏规则他应该不那么容易死,睡觉回血什么的都是标准流程。
可他好像悲催的记起来,他有先心病,虽然不严重,也早在幼儿园不怎么记事的年纪便治好了,二十年来他就是正常健康的人,以至于他几乎都不记得他还有过大病手术的经历。
很低概率会复发,但万一呢?
万一现实世界里他的心脏真的开始出现问题,那可不妙。他要赶紧回去才行,不能再抱着游戏人间,哦不对,是游戏“游戏”的态度拖延下去了。
那颗什么蛰甘草的功效似乎也不那么管用,他整日不说喝药,就是喝水吃粥也觉得胃疼想吐。
玩个游戏而已,他居然几乎日日像是快死了一样难受,真是玩够了!
容澜正心烦意乱,马车忽然一个急刹,将他甩到车门边。
“公子!快跑!快跑!”张喜的声音从车前飞速绕到车后。
车门“碰”地被人打开,风雪呼啸着吹了容澜一脸。
白皑皑的雪地里,张喜趴在上面,身旁殷红的血格外刺眼。
“公子!快……”张喜费力抬头,话说半句头便又垂下,然后再没有动。
王褚风也在马车里,他急急跳下车,去看张喜,瞬间两柄刀架上他的脖子。
远处打斗声越来越响,容澜久久盯着张喜的尸体胃里阵阵翻腾。
这不是他见过的第一个死人,淇县那么多尸体从雪下面挖出来,再往前说,他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死在自己面前。
可这是第一个临死前与他说话的人,是第一个临死还记挂他的人,这种感觉很奇特,让容澜一瞬间悲从中来,不是自胃里,而是由心里,吐出一口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