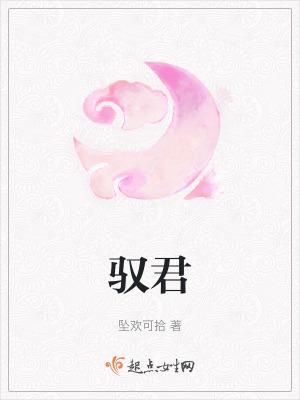片刻后,邬瑾小心谨慎捧着字帖回到偏殿,走到桌边坐下,打开发黄绢帛,看残纸题签上「晋平原内史陆机士衡书」几字。
看过后,他看题签下方,钤有双连珠印:「这是玺印。」
他再轻轻展开一部分:「骑缝处这一枚印看不大清楚。」
程廷心想:「看不清就别看了,喝茶。」
莫聆风心中暗笑,伸头看了一眼:「是‘莫失"二字,有这个印章传下来。」
邬瑾身心都落在帖上,完全没注意到程廷,转而去看陆机字迹:「当真是活泼可爱。」
程廷嘴唇沾在牙齿上,心想:「我也挺活泼可爱的,你看看我都渴成什么样了。」
幸而邬瑾没在此时细看字帖,而是先寻个匣子装起来,再回来坐下,给程廷倒上一盏茶。
程廷端起茶盏,一饮而尽,不敢发出喟叹之声,放下茶盏,低眉顺眼坐好。
脑袋上还一抽一抽的疼,他悄悄嘶了口气,忍不住道:「这老家伙,没想到手劲这么大,差点就破相了。」
莫聆风平淡道:「脑子没多大用,破相也没事。」
程廷连忙把脸扭向邬瑾:「正是因为脑袋没用,才要靠脸凑数。」
莫聆风勾着嘴角,哼哼地笑了两声:「也勉强算是五官齐全。」
程廷让她损了几句,不敢生气,岔开话头:「我饿了。」
莫聆风扭头看向宫人:「传膳。」
一顿不早不晚的饭很快由宫人提上来,摆满一桌。
程廷低头细看,见并非那种冰冷精致的花花朵朵,和莫府菜色相差无几,米饭配的一瓮炖羊肉,一碗豆腐辣羹,一碟蒸干肉,一碟蜜藕,一碟炸鱼。
这种熟悉的菜色让他放松下来,仿佛莫聆风还是那个莫聆风,他们三个还是围坐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挚友。
邬瑾起身,把豆腐辣羹换到程廷跟前:「吃吧。」
程廷不爱吃甜滋滋的菜,拿起勺子,舀一勺豆腐辣羹在碗里,和饭一起拌匀,再浇一勺,再拌,等饭里全是汤汁和豆腐,端起碗送到嘴边开吃。
他整个人都浸在食物香气里,一碗饭下肚,他身心得到抚慰,甚至高兴起来。
虽然挨了罚,但他不后悔,莫聆风和邬瑾的事,他不说,谁来说,现在话说完了,他脑袋上这一下也算挨的值了。
风卷残云吃过这顿饭,他掏出帕子擦嘴,吃的昏头昏脑,一边打嗝一边往椅子里坍塌。
宫女千手观音似的撤走残羹冷炙,开窗熏香,又悄无声息送上茶点。
莫聆风低声和邬瑾在说什么,似乎是说什么日子好,他全没留意,片刻后两人起身,往正殿而去。
程廷呆着脸跟上去,摸着肚子看邬瑾磨墨,心想这是要写罚自己的敕令。
邬瑾磨好磨,放好墨锭,铺开一卷黄纸,从笔架山上挑下一支诸葛笔,等莫聆风旨意。
莫聆风负手立在案旁,凝神细思,直到程廷站的两腿发麻,环顾四周,看有没有凳子坐下时,她才开口。
「今朕握符御宇,受命苍穹,国储乃建国所系,朕敦叙人伦,执宰邬瑾,邦国治世之能臣,器量宏大,胸吞百川,风度端凝,敏而内秀,英俊之才,足以配君王之偶,承宗鹢辅佐之任,虽登金台之侧,不拘彤庭,择八月十九日,简备典礼,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不拘彤庭,便是两全之策,典礼无所谓繁简,能够布告天下,就是大喜。
他是她的男人,同时也是君王的臣子,他有他应得的尊重。
程廷昏昏沉沉的脑袋,一瞬间清醒过来,嘴角咧开到耳朵:「这就行了?」
莫聆风点头:「用过宝印后,明日常朝,示下即可。」
程廷眼睛里突然有了巨大的喜悦。
明明他在诏书中并没有姓名,却比有姓名者还要激动,笑着笑着,他忽然在喜悦中生出一股伤感——情绪毫无来由的低落,眼里倏地有了热泪。
他不好意思哭,仰起头,使劲眨眼睛,但泪还是不断往上涌,就连喉头都哽住了。
他果断转身,大步走到窗边,狠狠吸了吸鼻涕。
许是因为他是旁观者,是亲历者,是见证者。
他想起他们三人第一次在州学相聚时,老黄狗还在,他还懵懂无知,围着莫聆风献殷勤,请她骑狗。
那时邬瑾还是卖饼郎,莫聆风还是娇娇女,他们笑容明媚,心似琉璃,都没有经历过惊心动魄的谋算、杀戮、伤痛、分离。
如果能预知将来,在他们相聚的那一刻,一定是心动有声,波澜壮阔。
邬瑾走到他身边,手掌按上他肩头,重重摩挲两下,柔声道:「都过去了。」
他懂程廷无法言喻的悲意,自己则像是深潭,不悲不喜,接纳这一份赤诚之心。
程廷抬手,用手背擦去眼泪,再次恢复豪杰本色:「行了,我回去挨揍。」
他视死如归地告退,邬瑾和他一起出宫门,又送他回家,再去值房处理政事,直到亥时初刻才归家。
陪着父母坐了片刻,他又临了两张陆机的字,亥时末刻洗漱更衣,吹熄灯火,筋疲力尽躺在床上。
两手交叉枕在脑后,他在黑暗中睁着双眼,人藏在夜色里,快乐从心底涌上来,撑破心房,蔓延到眼角眉梢。
嘴角慢慢勾出笑,门外忽然传来叩门声,是邬意来了。
邬瑾的心绪瞬间收拢,披衣起身,点燃油灯,给邬意开门。
「哥,我想新开个铺子,你能不能给我提个匾额?」
「写什么?」
「邬家糖铺。」
邬瑾道:「陛下今日罚了程三爷。」
「啊?」邬意很是诧异,「陛下和程三爷不是……」
他转眼就明白了邬瑾的意思——陛下连程三爷都罚,他要是敢打着邬瑾的幌子出去胡作非为,谁都保不住他。
他连忙站直身体,做出保证:「哥,我就开糖铺,真的,我刚刚从糖铺里回来。」
邬瑾看他战战兢兢的模样,点头道:「明天来拿,回去吧。」
「知道了。」
邬意匆匆离去,邬瑾没有睡意,干脆走去东隔间,磨墨铺纸,打算提字,然而笔握在手里,半晌没动,反倒在纸上滴了一大团墨。
他又想起莫聆风,想起明日要示下的敕令,烟消云散的喜悦再一次袭来,让他连笔也握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