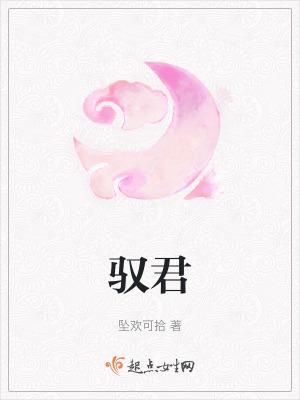宫城中,莫聆风沐浴更衣,没有珠翠满头,头发挽一个高髻,戴金冠,身着玄色龙袍,威严庄重,鲜少离身的金项圈取下,上朝时不再配戴。
她并非依附权利的女眷,而是手握利剑的天子,她的威重姿态,不需任何金玉点缀。
屋中纱笼里烛火明亮,程家大姐掌内宫六司,官从五品,为六司使,着青色长衫,高髻一丝不乱,头上簪一朵木芙蓉,还未显怀,护送莫聆风上撵驾。
莫聆风抬头看一眼头顶天幕。
寅时末刻,月已落下,天色青而薄,如同梅子色瓷器釉面,温润柔和,照物有光。
这般日夜交替之景,日后她将无数次看到。
她收回目光,一手撩起衣摆,登上舆撵。
程家大姐伴驾到紫微殿外,紫微殿前后都有殿门,御驾到紫微殿后门停下,后门外禁军列队,甲胄披身,手握长刀,护卫莫聆风入内。
后门前方,是一块影壁,朱红屏框,屏心内雕刻金龙,面向紫微大殿的那一面雕刻一只金凤,四角蝠流云纹,左右两侧是山水屏风。
莫聆风下撵驾后,殿内禁军立刻带刀登上丹墀,立于御座后。
没有伞盖、团扇,没有内侍、宫女,只有毫无温度的铁甲、长刀,震慑忠心、疑心、反叛心。
在莫聆风之前进入殿中的官员顿时噤若寒蝉,手持笏板等候君王。
莫聆风迈过门槛,绕过屏风,在百官注视下登上金台,脚下群臣在礼官引领下,行一跪三拜大礼。
他们匍匐在女子脚下,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神情恭顺,在他们三呼万岁时,声音在紫微殿回荡,大殿中的金银玉器都似乎因此震动。
等到余音散去,莫聆风才淡笑道:「平身。」
朝臣起身,禀笏而立。
皇帝目光扫向他们,他们心中立刻就是一滞,畏惧之感油然而生——莫聆风不是仁义君主,在战场上的种种血腥手段,已经深刻他们心底,仿佛她多看一眼,他们就会血溅三尺。
加上近日诸事太平,并无要紧事启奏,一时满殿寂静。
莫聆风见人人恭谨,无人奏事,先开金口:「自朕祭天以来,国中风调雨顺,文武齐心,百姓安乐,城池坚固,唯有两封国书,不尽人意,大昭撕毁国书,不缔友好之盟,金朝国书气焰嚣张,殷监军使——」
殷南聚精会神听莫聆风说话,但是对「殷监军使」四个字没有任何反应,站在她前头的游牧卿只能往后撇腿,踩她一脚。
殷南这才反应过来,一步出列,躬身道:「陛下。」
莫聆风先是一笑,笑意转瞬即逝,正了脸色:「我与金虏有九世之仇,你是国朝肱骨,堡寨砥柱,对金虏,凡是越国界者,不可错放一人!」
「是!」殷南昂首怒喝一声,其他朝臣跟着哆嗦了一下。
待殷南归位,莫聆风再谈小报上的武德司——她说起大昭举动时的神情,漫不经心,仿佛大昭已是笼中物,赵湛的任何举动对她而言都微不足道,不会打乱她的步伐。
大岐臣子心中有底,不再慌张,能够对答如流,同时大部分人都曾是大昭朝官,心底难免有几分怅然。
过后,莫聆风再问水师一事:「济州市舶司水师近况如何?」
何卿本就害怕莫聆风,听莫聆风点到市舶司,心里咯噔一下,不得不出列,禀笏躬身道:「回陛下,济州驻军已组建水师两个营,共一千人,在济州码头外训练,正习泅渡之术,不日便可越深水渡江河。」
他又慌里慌张说起战舰:「建有十艘戈船......」
程廷跟何卿之间隔着三个人,百无聊赖,悄悄乱看,先看一眼他的老父
亲,再看一眼莫聆风,明明御座上坐的是他从小看到大的人,但绝不是他熟悉的莫聆风。
这个莫聆风身后是明晃晃的刀光,面目清晰,两眼线条锋利,足以抹杀一切情义。
在莫聆风看过来时,他竟然惊的一颗心猛的往下一坠,慌忙低下头去,片刻后才回过神来。
没有莫千澜的莫聆风,太过冷漠、坚硬、理智,少了人味。
何卿还在流水似的说,他轻轻呼出一口气,又用余光看向邬瑾。
邬瑾在文官之首,站的笔直,气度与明亮肃穆的朝堂很契合,英俊,沉稳,和颜悦色,任何人看了都会相信他,亲近他,哪怕是莫千澜,最终也会对他和盘托出。
他如老僧入定,圆满湛寂,如大圆镜,万象森罗,山河大地,影现其中。
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可惜——他终其一生,不会有家。
不必入赘文书,国朝、君王、百姓,已经是一张巨大罗网,织出千丝万缕,牢牢将他网在其中,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程廷收回目光,没再东张西望,垂头看自己的乌皮靴,忘心想这大殿里最尊贵的两个人,都不圆满。
他可怜他们,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何卿啰啰嗦嗦,总算说完入列,在短暂的安静里,程廷持竹笏一个箭步出列,朗声道:「陛下!」
他嗓门本就不小,一时激动,更是声震屋瓦,程泰山脑子里登时绷紧一根弦,恨不能捂住程廷的嘴,把程廷从这威严之地拖出去。
他微微抬头,看一眼莫聆风,见莫聆风嘴角带笑,并无恼怒之色,稍稍放心。
莫聆风道:「何事,奏吧。」
程廷在众人灼灼目光下,豪不慌张:「陛下,臣以为如今国土虽只有四州,但兵强马壮,国库满仓,水师不日就可以开拔,开疆拓土并非难事,陛下已不必多虑,反倒有一桩大事,陛下不可不忧。」
他停顿一下,大声道:「国储乃国之基石,陛下年过二十,可以择婿。」
程廷所说之事,朝中确实无人思虑,此时他忽然提起,众人一时哑然,更不知女帝该如何选夫。
黄韫书悄悄看一眼邬瑾,心想女皇要选夫,这位可怎么办呢?
这位是丞相之才,绝不能养到深宫里去,但看他与陛下相处,彼此又有情义,难不成要身居高位,孤独终老?
程泰山悬着的心放了下去,又侧头看一眼邬瑾,邬瑾神情恭谨,没有因程廷的言语起伏。
正当他思虑要如何将此事圆过去时,侯赋中出列道:「陛下,不如择、择上……」
这话说着说着,他有点说不下去——金台上坐的若是男子,便可三宫六院,粉黛三千,如今换成女子,择上几个男子的话就说不出口,仿佛自己也跟着受了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