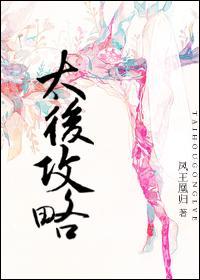这一日瑶华宫递来帖子,道丽修容宴请六宫嫔妃赏荷品酒。
林云熙算算去行宫的日子,便让秦路备下轿辇,再去请敬和夫人同行。不多时,敬和夫人与胡青青联袂而来。敬和夫人绿裙,耳畔一对明珠如月晶莹,婷婷袅袅,胡青青着翠色蝴蝶缠枝花卉纹暗花罗襦,执一柄白底兰草素绢团扇。深碧浅青,具是清新温婉的风姿,一眼望去甚是相似,林云熙不由笑道:“你们倒像说好了似的,如今连衣裳都换着穿,真真像是两姊妹了。”
胡青青笑道:“难得昭仪愿意出门走动,妾身等哪里敢不奉陪呢。”敬和夫人亦笑道:“昭仪与胡妹妹即要随驾避暑,可不得多见几回。不然到了行宫里,昭仪有胡妹妹相伴,只怕连妾身是什么模样都记不得了。”
林云熙点了点敬和夫人,笑道:“你这做姐姐的,竟和妹妹吃起醋来了。”
三人说笑一阵,收拾停当,乘了轿辇一道往瑶华宫去。
瑶华宫在上林苑的东北角上,宫中玉宇琼楼,画栋雕檐,遍植仙花异草,一道溪流自宫墙环绕流入其中,凝成清浅一湖静水流深。湖边水榭珠帘绣幕,鼎焚百合之香,苍松碧树,怪石假山嶙峋,山顶处一座凉亭,飞檐上挂着八角风铃,随微风当啷脆响。
林云熙到时并不算晚,丽修容十分客气得将她迎进水榭中。婉容华、忻婕妤、胡青青等一干嫔妃已然在座,起身向她行礼问安。林云熙微微颔首,示意众人起来,笑道:“不必多礼。今日是丽修容做东,咱们客随主便就是了。”
丽修容依旧清冷艳丽,但神色却显得和气温柔许多,此时也稍稍勾起唇角,温言道:“都是自家姐妹,又是难得欢宴,何须拘束?诸位姐妹随意即可。”
拍手示意宫人送上宴饮瓜果酒水,命乐师舞姬奏乐起舞,一连先敬三杯。众人不好驳她面子,也随之入席,饮酒观舞。一时席上渐渐热闹,取来花名长签行起酒令来。
诸妃以林云熙为首,她便先抽一签,竟是一株娇艳欲滴的石榴花,上题“东风如意”,又注一句诗曰:“紫府真人饷露馕。”心头微微一惊,看了众人一眼,紫府真人主东华帝君,石榴有多子之意,这签的意思便有些微妙了。
众嫔妃中精通诗书的不少,酒宴上却只作寻常诗文罢了。她略放下心,转瞬又想,不过寻常酒令上用的花签,她一向连三清面前求来的卜文都不信,何况这个?稍稍思考,便笑道:“焕若隋珠耀重渊。”
丽修容忙叫宫人倒酒,笑道:“这句意思不错,却错了韵了。”
林云熙笑道:“看你一会儿能说得几句不错韵的来。”
几轮下来,林云熙也喝了不少,不由玉容绯红,面上如烧。诸妃酒酣微醉,敬和夫人笑吟吟道:“丽妹妹请咱们来看花,如今花还未见着呢!”
丽修容双颊盈一抹粉色,更显妩媚动人,笑道:“自然是要给诸位姐妹开眼的。”
吩咐宫人抬了一瓮古铜大缸来,缸中荷叶层层叠叠,青翠欲滴,偶有金红小鱼自叶下浮游而过,甚是可爱。满目碧绿,已有坐不住的嫔妃窃窃私语道:“不是说赏荷?荷花在哪儿?”
林云熙眼尖,脱口道:“这是绿荷?”
众人忙再看去,果然重重荷叶间,翠绿的花瓣绽放,端庄怡然,清新娇妍,只是与荷叶一色,难以分辨。
婉容华抚掌笑道:“果然是荷中珍品!这绿荷独岭南所有,且只养在布山县一条清溪之中。其余任那处泉水再清、泥土再浊,也是养不住的。丽妹妹竟把这绿荷养到宫中来了,可叫姐姐长了见识了。”
嫔妃们的目光都围着绿荷打转,有几分见识的都知这绿荷难得,莫说绿菊绿梅,就是牡丹之中的姚黄魏紫,也未必有这个罕见。丽修容道:“我宫里新进了几个花匠,也是他们有心,千辛万苦植了出来。不止绿荷,还有不少逸仙莲、绮菱、冰娇,都养在宫里。诸位姐妹若想瞧个新鲜,不妨自便。”
林云熙含笑挽了敬和夫人的手,道:“可得好好瞧瞧,那绮菱是不是真的只有拇指大小。姐姐与我同去,如何?”
敬和夫人不由带了几分受宠若惊,忙笑着应承了。她二人一走,剩下的嫔妃也都三三两两散了开来,各自赏花吟诗去了。
林云熙二人沿湖畔假山拾级而上,山顶凉亭中正供着一瓮绮菱,小巧玲珑,深碧浅红,婷婷玉立。敬和夫人不由赞道:“这等珍品,确实难得。”
胡青青恰好在她们后头一步,带了瑶华宫的宫人上来侍奉茶果,闻言笑道:“绮菱俏丽,不过小巧而已。妾身前些日子在昭仪宫里见到一瓮并蒂待放的小舞妃,那才叫美不胜收呢。”
林云熙笑道:“这两日那花开了,好看的很,得了闲也请你们来瞧瞧。”
敬和夫人讨巧道:“昭仪向来得圣人敬重,也难怪并蒂莲这样的好兆头都开在昭仪宫里。”
林云熙微微含笑不语,胡青青以扇掩唇,笑道:“敬和姐姐不知道,花是圣人送去昭阳殿的。”
敬和夫人也随之拿纨扇遮了半脸,吟吟而笑。
林云熙耳根微热,面上却平静如常,笑道:“不过一盆莲花罢了,也算不得什么好东西。”
敬和夫人道:“凭什么花再珍贵,咱们也不是没见过。只是圣人的心意难得。可见这宫中,再没有比昭仪更得圣心的了。”
她似笑非笑地睨了敬和夫人一眼。敬和夫人自觉言语有失,忙扯开话题道:“说来昭仪正当盛年,只怕没多久,又能为小皇子添一位弟弟了。”
林云熙端起茶抿了一口,微微蹙眉吩咐一旁侍奉的宫人道:“茶凉了,去换一盏来。”
几个宫人不敢怠慢,连忙应声去了。
胡青青笑着打圆场,道:“妾身方才看敬和姐姐在宴上多饮了几杯,许是有些醉了。宫里能说知心话的人少,也就是昭仪面前,才敢松快些。”
林云熙并不领情,淡淡道:“中宫尚在,换了是我,可是万万不敢如此放肆的。”
胡青青不由一张脸通红,敬和夫人一时又急又羞又怕,面色紫涨。含愧起身请罪道:“妾身言辞不慎,请昭仪恕罪。”
林云熙本就不欲为难,只不想让人得寸进尺、借机攀附,便也重拿轻放,道:“罢了。我不过是提醒夫人一句。”
亭中一时寂寂,敬和夫人原本打算和林云熙说秦氏伴驾之事,也是丝毫不敢开口了。更无颜继续陪坐,正欲告退,明日再往昭阳殿登门请罪,便听林云熙道:“且不论皇后,圣人以孝治天下,在圣人心里,自然是太皇太后最重的。”
敬和夫人虽不知林云熙提起太皇太后的用意,但见林云熙没有驱逐她的意思,已经十分惊喜,也厚着脸皮留下来,忙不迭束手拜道:“是。妾身谨遵昭仪教诲。”
胡青青颇有些错愕得看了敬和夫人一眼,垂下眼眸没说什么。
林云熙见两人情状,心下暗笑,胡青青毕竟年轻,敬和夫人到底不同,她不过模棱两可一句话,就能自己搭起梯子顺势下来,也难怪从前恩宠不少。
她不理敬和夫人,转而问胡青青道:“我听闻太皇太后这些天身子不大痛快,嫔妃里你素来最孝顺她老人家,可知太皇太后好些没有?”
胡青青一怔,余光飞快扫过敬和夫人,随即脸上已是温婉关切的姿态。无论林云熙为何问起此事,昭仪既想听,她自然要说得事无巨细,娓娓柔声道:“妾身最近去寿康宫请安,太皇太后确实有些疲倦。大约是天气热了,文贞夫人又一直病着,太皇太后挂着心,故而不大舒坦。不过太医们一日三次去诊平安脉,只说太皇太后上了年纪,好好静养也就没事了。”
林云熙微微笑道:“如此便好。圣人去行宫本就是为了避暑,好松快些。太皇太后无事,又有皇后娘娘照顾,想来圣人也能放心。”
细细与胡青青说几句行宫中的情景,“你之前没去过,去了就知道。行宫里湖光山色,风景甚美,又凉快。山里头灵气足,还建了一座太平观。”林云熙笑意盈盈,宛如平日里与姊妹细语,“太皇太后信道,你正好能为她去打醮祈福,好好抄些经文供奉。”
胡青青忙道:“果真么?那再好不过了,不知道观在行宫何处,可有真人在观中修行?主奉的又是哪位仙尊?”她问的急切,十分情真,亭中诸人纷纷笑了。林云熙也笑道:“你这倒是问住我了。我只记得观中有位清妙真人,乃是胶东王姬,道法精妙。你若有心,遣人去打探一番便是。”
胡青青方显出不好意思的神情,林云熙和声道:“太平观在永安殿边上,以往太皇太后去行宫,就住在此处。永安殿靠山临水,论清凉避暑,还在圣人所住的翠微殿之上。”
敬和夫人忙笑道:“圣人真是孝顺。”
林云熙道:“永安殿素来是国母居所,自前朝起便有十数位圣人奉太后于此静养。别的不说,单咱们大宋开国,已有六位太后、两位太皇太后住过。”她神情澹然,于此间典故如信手拈来,“孝武帝时因永安皇后侍太后于万方殿,孝名传天下,后来永安皇后为太后、太皇太后时又得子孙孝顺,颐养天年,过茶寿含笑而逝,故其孙文忠帝将万方殿改名为永安殿,以示孝心。”
敬和夫人二人露出恍然之色,胡青青神色微微一闪,婉然道:“圣人以孝传家,果然堪为天下表率。可惜太皇太后需静养,不好轻易挪动,不然奉太皇太后去行宫养病更为相宜呢。”摇着纨扇,好似玩笑般道:“传出去可也是一段嘉话。”
林云熙目中略带赞赏,盈盈浅笑道:“虽说有后妃侍疾的旧例,不过皇后娘娘留在宫中亲自照料,想来是无大碍的。”
敬和夫人怔怔听了半晌,后妃侍疾、皇后亲自照料——皇后就算为太皇太后侍疾,也不会亲自侍奉汤药,无外是垂询太医、陪伴在侧以示关切,多半是由宫人或位份低下的嫔妃伺候。
——永安皇后、后妃侍疾、低位嫔妃。
她忽然升起一个念头,心下不由怦怦直跳,背后一阵燥一阵寒。
林云熙含了几分清浅笑意,对敬和夫人道:“过些日子咱们与圣人去了西山,宫中除了皇后娘娘,便是敬姐姐为尊了。姐姐可要好好协助皇后,为太皇太后侍疾啊。”
敬和夫人只一味出神,胡青青忙轻轻推了她一把,笑道:“敬和姐姐想什么呢?”她方才像大梦初醒般回过神来,慌忙道:“是。”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林云熙笑道:“皇后娘娘虽不如当年永安皇后孝名显著,可对太皇太后的孝心却是世人皆知的。来日敬姐姐与皇后娘娘一同侍奉太皇太后,还要妥帖些才好。明白吗?”
敬和夫人骤然一惊,阳光随亭角飞檐落下来照射在她手背上,仿佛能刺痛肌肤一般。她缩了缩手,才发觉背后大汗淋漓,像是有什么在身后威压逼迫,令她忍不住心生恐惧。
林云熙只一壁温婉含笑,神情从容平静。
她知道敬和夫人听得懂,也不会拒绝。
果然,最终敬和夫人静默片刻,笑意嫣然地起身福礼,恭敬道:“是。妾身明白。多谢昭仪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