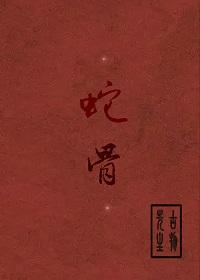火气不打一处来,又想着破甚么阵,不破了!直接搞坏这个阵,那祝傥肯定也会感应到自己的怒火。
可是真想搞坏这阵也有点难度,起先还燥的很,後来拆着拆着上瘾了,季清流心情也慢慢平复了些,最后索性专心致志的只在意眼前剩下的这几个小阵眼了。
祝傥急匆匆回来时就见着幽季衣衫不整披头散发且坐姿十分不雅的抱着那阵看的起劲。
又顺着他完全没介意开合与否的衣袍,露出来的半边白皙大腿,衣衫也快堆叠到肘部了,眼睛却仍旧紧锁着阵势,完全一副心无旁骛的模样。
想着不悦,却没打扰他,回头去问了站在外头冻得浑身发抖的苏管,「进去过没?」
苏管忙摆手,看祝傥这表情就知道帝君在里头是一副怎样的架势了,心道还好自己没进去。
於是祝傥又略觉宽心,再度走进了屋。
将衣袍给他整的稍微齐了些,季清流才刚刚回神。
瞧见这摆阵之人回来了,索性将这小木头阵往他怀里一砸,「甚么玩意儿,眼见着能开了又覆了一个星阵,我他娘现在法力不在,怎么推测星象?!你故意惹我不开心?你闲的啊!」
祝傥也没料到他这么大火气,又想着这是有积怨,不再去恼他,只将这木头渣滓自怀里扑棱开,淡道了句,「那不破了。」
又忍不住将衣袍给他再整了些,祝傥轻声道,「去洗把脸吧,一会儿准备吃饭了。」
说着自己便当先要往后厨里走。
季清流单腿伸下床,单腿仍旧别在身下,不为所动。
祝傥也是换了衣服进了后厨才想起这话不对,於是又忙亲自断了盆温度合适的水回来,声色也有些不同于往常,「抱歉……我今天有点忙,忘了这茬。」
说着又要服侍他洗脸。
季清流一手从他手里揪过毛巾,不耐烦的挥手,「滚滚滚,看见你心烦。」
祝傥又笑,看着他好似没将这事往心里去就放心许多,再度思虑重重的往后厨走了。
得了祝傥回来,有更强的仙火燃着取暖,苏管也暖和过来了,又在外头继续准备那一大堆将来要给祝傥用的药材,一边心下感叹道:
喜欢帝君有甚么好啊,简直整了个爹回来啊。
不对,这何止是爹啊,这得是祖宗。
又惊叹道:想的没错,这确实是个祖宗。
吃了饭祝傥不知又和苏管有甚么大事要商谈,进了那间小屋。
他想去听听,可又觉得被发现了不好意思,一时闲在屋里又无所事事,寻思着,刚才发那么大火摔坏那木阵干嘛呢,不然好歹还有个可供解乏的东西。
想着又对那窗扇打起了主意,反正自己现在鬼术强了些……翻窗跑也不是没可能。
只不过往往这种念头刚起,祝傥就回来了。
往他怀里塞了几本书,季清流接过,打眼一看,全都是甚么玄清术法的,因此更是发了火气摔他个劈头盖脸,「给我这玩意儿干嘛?我又没术法,修不了!」
祝傥也不恼,只轻声安抚他道,「那你也多少看看吧,别把一些最基本的都忘了……指不定哪一天就又派上用场了呢?」
蹲下身来仔仔细细一本一本重新拾起了,祝傥往桌边一放,温言劝道:「要是实在不想看,也别扔。刚才把我的小木阵给毁了,我跟苏管谈事你没事干的时候,有没有后悔当时发脾气了?」
季清流冷笑一声,「没有。那东西看着碍眼,当扔则扔!」
祝傥又无奈,将他往怀里揽了一揽,声色暖迸,「其实幽冥也都是想对你好的,你一直不领情便算,还要拂了人家美意。以后脾气也稍微收敛下,这天底下又不是所有人都叫祝傥,能这么惯着你。」
季清流见他这话说的怪渗的,又想起他刚才一回来时音色好像有一种倦意,更不知此刻是怎么了。
刚想问,又听他道,「今天有些累了,陪我早点睡好吗?」
能早点睡不折腾自己,他自然也是巴不得。
可就是因为这种感觉——这种祝傥在逃避甚么一样的感觉,让他不自在。
虽然跟他一起躺下了,季清流还是忍不住小小声问道,「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吧?你不会……和幽冥要联手对付我了吧……」
祝傥又一睁眼,忍不住凑过去在他脖颈上狠吸了一口,这才心满意足的躺回去道,「幽季,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睡吧。」
「真的?」
「嗯,真的。」
虽然心下怪怪的,可是,可是祝傥这话好像又尚且有几分可信度。
再说了,枳楛带着阿啾前几天也来了一趟,说是幽冥前些日子擅离冥府就累下一大堆事没能及时处理,近来又更是是非多,一时半会儿,怕是抽不出空来陲城亲自抓自己回去认错。
当时听他俩如此说,自己曾笑笑的点头应了。可是他俩脸上表情不对啊……
季清流心下也开始慢慢发寒,怎么就觉得,怪怪的呢……
「也没叫你们来抓我?」
枳楛一愣,随即连连摇头,「我们又打不过祝大哥。」
祝大哥。
这个称呼,好像有多熟一样……怪哉怪哉。
面上干笑了两声,不及再试着问些话,祝傥就进来了,枳楛和阿啾也不敢再多留,向他道了个好,同自己道了个别,接着就和惊弓之鸟一样的跑了。
那时候季清流坐在床边上摸着脖子,莫名就觉得,有些寒。
可是……一切又都正常。
除了祝傥好像越来越找不见人影了。
这一夜虽然睡的安稳,可脑子里却想东想西了好多事情,飘飘然又空落落的,甚么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都过了一遍似的。
等着他这一觉悠悠醒来,不等抱着绵柔的锦被再蹭一蹭,再舒舒服服的伸个懒腰……
一个呼吸不当卷入鼻腔一口冰凉的气息,他就忍不住蹙着眉睁开了眼。
虽然这几天祝傥也都是先他醒先他离开床榻,但是他的仙火还都燃着,为自己供着源源不断的暖意。
此刻想像往常一样的舒展胳膊,才发现一露出来都跟直接伸进冰窟里似的,冷的要死,略停留在外头几分钟就跟活生生能冻掉了似的。
这么想着便扭头去寻桌边暖茶,想看看祝傥是不是连自己的这点习惯都忘了。
忙甚么事能叫他忙成这样?!
这么一扭头才发现……桌子……不对!
床还是他自己的,被子枕头甚么的也都没变,也是放在靠着墙的位置,只不过这屋子大体上的装饰全都不一样了!
想着便一把掀开被子,也顾不得冷,只不过没有祝傥给他穿那么麻烦的衣服他也就懒得自己动手,松松闲闲的往腰上一系,刚准备下床去看看这是怎么了,没想到一条腿刚伸,一只手刚抚上床榻,季清流就一瞬间愣住了。
随即不可置信的将手抬到自己眼前,翻来覆去的看了会儿。
然后,他咽了口唾沫。
似乎有点不可置信,再度微微将手平伸于自己眼前,一拈,一张……
一条玄冰寒龙直接从手心猛蹿而出,眨眼便卷破了眼前房门。
法、法力回来了?!
他大喜过望,又忍不住站起身扭转了会腰脊——好像确实是他自己的骨头,没有任何不适之感!
再度忍不住抬了抬胳膊,後来索性在空中直接翻了一圈,接着便腾云驾雾的直冲出门。
迅猛的玄清之气绕身狂旋不歇,周边缭绕的鬼雾也统统退散,似乎很是畏惧他身上的仙家真气。
这狂卷不止的风吹起他一头未系的青丝,负手而立于云端之上,叫他忍不住就想吐口气。
这一口气就能吐出个狂风巨浪吐出片洪荒天怒,一下子将幽冥这里拍个稀巴烂。
早就想这么干了!
只是还不等他泄愤一样的把这里摧毁,眼风一扫就见着一群人正在忙碌的进进出出,再仔细一凝目,就看到幽冥正在那个小院里,抬头神色不善的打量他。
你打量个屁!
想着便直扑下来,随手空抓一把风气也能凝成把上好的宝剑——绝对比祝傥那把破剑锋利上不知几许,眼瞅着便要冲幽冥砍去。
幽冥周身黑雾一涨又一散,再出现时已在另一个方位了,躲开他这一招更是懒得还招,幽冥冷声道,「你再多放几招出来,里头那人受你波及,命就真捡不回来了。」
甚么意思?
幽季不解的扭回头往屋子里看。
刚一回首,身后忽然贴上了幽冥冰冷的身子,感受到他的手已经按上自己心肺,幽季下意识一颤,恨声道,「你耍诈!」
「我耍个屁诈!我是真恨不得把你这身脊梁骨再给你抽出来!你留着有甚么用?你除了会耀武扬威炫耀你那真身不凡外,你还会干点甚么?你从小到大办过一件正经事么?替那些心心念念着你的人分过丁点忧了么?」
是恨铁不成钢的又推了他一把,将他差点直接推跪到屋门口,「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人家祝傥不欠你甚么。」
渐行渐远的冥主忽又顿住,「对了,祝傥让我教他这个『移愆』的天刑截罚之术时,可是跟我立过誓,自此之后,要替冥府办事了。」
甚么?!
幽季还不及回头问问他这句话是几个意思。
就听幽冥冷声道,「所以我一开始不同意他这么做,因为他和你不同,他不是烛龙,没你真身庇佑,恐是难撑此劫。但他说他能撑过去,我就信了。」
「你也知道,我冥府事务繁多,要他祝傥是看中他的精明能干,至少比你有用多了。但是若因此举他不幸身亡,那我……可也难压住我的脾气了。」
说罢一甩袍袖,黑雾一散。
幽季有点懵,然后慢腾腾的爬起来,立在门口,想了会儿。
想明白了后接着抬腿便要跑。
好巧不巧,他刚打算逃之大吉方为上策之时,就见阿啾又抱着一大堆药材急冲冲进来了。
少年一双水灵清澈的大眼就这么眨也不眨的将他望着。
然后怯声道,「季大哥你也是来帮忙的么?」
我……我怎么可能是来帮忙的!
他爱死不死!
又想着,自己身上之所以无痛无灾,是因那劫难全让祝傥转移到他自己身上去了。
浊灭池上那钻心蚀骨的痛楚他现今想来还全都是后怕,那祝傥替自己受了两次——一次除掉己身上的蛇骨,一次再融回烛龙之身……
此刻哪里还能捡到甚么活头。
简直是自不量力,老子还是因真身不凡当初才敢上的浊灭池,你以为你法力无边就也能撑得过么?
那,那许不定这一眼也就是最后一眼了,都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那自己也不好真就这么跑吧。
更何况还被直接堵在了门口……这时候再跑多没面子啊……
於是又只好干笑着答了句是啊……
然后硬着头皮往里头走。
不及走近了,便瞧见堂屋走来走去的十二个鬼医,似乎是在踏着甚么阵法,也好似是在行着甚么祈祷之事,里屋苏管和枳楛看似冷静却音色发颤的报着药名。
一时间倒让幽季心下慌乱的很,又觉得自己十分多余,不然还是退出去吧。
不料那边苏管又眼尖看到他了,忙道了句,「帝君快来!」
「我……」
我过去个屁啊……
「你跟他说会儿话,你多少说两句,他的希望可全都是你了啊……」
幽季硬着头皮继续往里迈,一步步都跟栓了幽冥那玄寒之铁似的,十分之让他抬不动腿。
这么一进里屋更是头皮发麻,一瞬间被震呆在原地。
床上那人双目紧闭,身上血色尽失,地上也是一片血红,全然、全然一副当年浊灭池上的惨象。
虽没那剔骨抽皮之声萦耳不绝,可看着他身上皮开肉绽的无数大小伤口,这副骇人的模样,到底还是把幽季看傻了。
枳楛起先忙着止血,没来得及骂苏管,此刻真得了幽季走进来了才捯饬出喘口气的功夫,手下也没闲着,「你别让季大哥看这些了,他看不得这个。」
忙扯了嗓子又道,「季大哥你快出去吧,别再被吓着了。」
苏管听得火大,一把摔了手里药材,更不知哪儿来的胆子,上前去一把揪过看呆了的幽季,将他一把扯到床前、扯到这完全像是救不活的祝傥身边,吼着他道,「现在都他娘这样了,你还因为这副场景丑不丑骇不骇人跟我计较?怎么,你觉得他现在这副样子丑的很可怕的很吗?!可他是你的祝傥啊!他是喜欢了你那么久为你做过那么多事的祝傥!」
苏管现在也快要炸了,「我他娘当初早就跟他说了,不行的,幽冥的这个法子根本行不通,因为你不一样,对,对对,你高贵,你是烛龙之身吗,你当初靠着真神撑下来一次,他祝傥一介凡胎罢了他靠甚么撑住两次反噬之痛?!」
「冥主倒也是个会推脱活的,纵使当初他来,他自己的麒麟身也难与你真神之骨匹配,血液里虽有丁点相像,可被那灵性充盈的烛龙之骨一旦察觉出不一样来,反噬之痛怕是他也受不住的!」
「祝傥还非要拦下这个活计来,我看他就是在找死!」
「当初喜欢上你我就跟他说过那是他在找死!」
「他回头来跟我说了这个法子我就跟他说了一百遍一千遍不行不行不行!可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甚么叫还了你骨头能哄得你开心!」
「劝了那么多遍都不听,一个两个的简直要叫你们气炸了!」
「老子不救了!」说着苏管气愤的摔了药材就要走。
这是真的没法救了。
这还是他昔日旧主。他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昨夜……昨夜他起术之时,苏管就在门口不忍心听。
那从骨骼深处传来的碾压之声,从喉咙深处硬生生挤回肺腑的难吼难言之痛。
明明身上无一处受伤……却慢慢从毛孔每一处渗透而出的红色血迹。
起先只是一小滩,苏管看见冒血了,便给他擦擦,及时的上上药,尔后越来越止不住……他神思也越来越恍惚。
可是他不能闭眼,更不能失神,因为他要操控,操控这替他受难的术法,要眼睁睁受痛同时感受这痛,他才能确认无误——那边的幽季正在平安无恙的进行着换骨过程。
只有自己痛着,才能明白,他现下不是痛着的那个。
等着好似得了幽冥终于出口的那声『好了』。
祝傥这才终于肯放任自己闭一会儿眼。
那个时候他浑身上下好像还正常的很。
可苏管却觉出一股子不对劲来,周边的气压好似都低了许多,紧绷压抑着,又似慢慢膨胀着……可感受了一番也不知究竟是甚么不对劲。
那时祝傥阖眼前十分微弱的道了句,「别叫他来……」
尔后浑身上下忽然爆裂开无数细小的口子,接着皮开肉绽声一片……更别提那直接喷涌而出的鲜血了……
苏管当时被喷了一身一脸,虽然阅病无数更是见过许多惨景,可好似是因为这是唯一一个他的主上,他的旧识,才被吓得神魂未稳。
待得回神还是因为祝傥好似略带笑意的最后一句——「他会害怕的。」
别叫他来,看到自己这副鬼样子,他会害怕的。
苏管当时已经说不出任何话来了。
当初那个叱咤天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祝傥呢?
彼时欣赏他的精明更佩服他的胆识,却没想到,也无非难逃情之一字。
你说你喜欢的是个值得你这样用心用力去对待的也好。
却偏偏……还是一个根本不拿你当回事的人!
祝傥,你傻不傻?
你傻透顶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