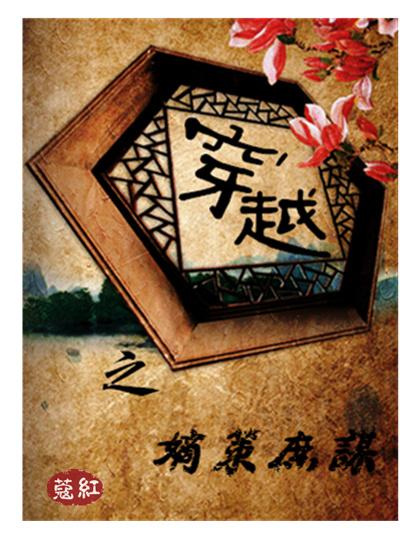一百证据确凿
刚出生的婴孩儿不及时清除口鼻中的秽物,即便不被闷死,也会因窒息而造成日后的不同程度的痴傻。
只是当时沈氏难产血崩,母子俱亡本也不稀罕,故而无人注意到,孩子刚出生时竟还活着。
舒恰会知道,也是极其偶然的。
都说产房是污秽之地,除了下人之外,一般主子都不会轻易踏足。
而舒恰当时也不知是存了怎样的心情——或是为了讨好沈氏,又或者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大约这就是冥冥之中有些事注定要浮出水面,舒恰她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竟毫不避嫌地进了产房。
只是也没待多久,便被稳婆给“请”了出去——而也就是这不多久的时间,她听见了一声短促的婴儿哭声。待她转过头去寻找的时候,那哭声又没有了。
而之后产房便传来噩耗,沈氏和孩子都没保住。
虽说自己并没有证据,可舒恰的心里到底是存了疑窦。她确定自己没有幻听,当时确实是听见孩子哭了——若是刚生下来没多久,说法又不一样了;可目前为止的说法就是难产血崩生下了死胎。
于是在那稳婆奉秦氏之命将那孩子偷偷拿去埋了的时候,舒恰便偷偷跟在后面,暗暗记下了孩子被埋的地点。
舒恰道:“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出了舒府,两人立即赶往舒恰所说埋藏婴儿尸体的地方。
果然在舒恰所说的那出,有一块明显松动过的土地。
贺峥道:“想来就是在这里了。”
许是近乡情怯,舒忱此刻站在贺峥的身后,竟再不肯往那处再靠近一步。
“……要不,我们先去找仵作?”贺峥心里也有点犯怵,挖坟这事儿他还真没干过。
好半天,舒忱才摇了摇头。
“先挖开,否则……若里面什么也没有,把仵作叫来了又有什么用?”
他倒不怕让仵作白跑一步,只怕这事情流传出去,让秦氏发觉了打草惊蛇。
他原本还没想好,沈氏真为秦氏所害,他该如何为母亲报仇呢?
可是现在,舒恰忽然告诉他,不止是沈氏,连那刚出生的孩子也是秦氏下的毒手。
……杀害庶子的罪责,可是要比杀害一个妾室来得重的。
舒忱镇定了一下,挽了挽袖子:“你走远一点,我来。”
“还是我来吧。”贺峥即便内心再犯怵,也不会让舒忱一个人动手,当下也挽起了袖子,就要开挖。
舒忱却拦住了他。
“不,你……他是我的弟弟,还是我来更合适一些。”
古人都比较迷信,舒忱也不能免俗。挖坟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那是大大的损阴德,不止如此还会使得去世的人不安。
贺峥对与这个孩子到底没有血缘关系,或许还是自己动手,那孩子会更理解一些吧。
舒忱把贺峥赶得远远的,自己则对着那一小片松动的土地念念有词了好一阵,无非是说什么“哥哥是为了给你和娘报仇才会这么做的,你千万不要怪哥哥,等哥哥给你和娘报过仇,一定给你建个更好的坟,再长长久久地给你供奉个长明灯……”
也不知那孩子听得听不到,听不听得懂。
大概这么念了一会儿,舒忱便开始动手挖了起来。
并没有挖很久。可能是那稳婆没想过会有人跟在她身后把地点记下来,草草的将孩子埋了,并没有埋很深。舒忱只挖了薄薄的一层土,就挖到了。
……
直到贺峥匆匆忙忙带了仵作过来,舒忱还保持着两手捧着那个孩子的姿势,一动也不动。
在贺峥的示意下,那仵作小心翼翼地从舒忱手里接过孩子的尸体。舒忱的手指动了动,却并没有拒绝。
贺峥走过去,轻轻把人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暖着舒忱发冷的身体。
那仵作是宁城派来的,想来很是可靠。现在手脚麻利地粗粗验过。
舒恰所说,只是她结合自己知道的常识所做的一个推测。可秦氏比她想象的要狠。
不清除口鼻秽物,也许会死,也许只是将来变得痴呆。可是秦氏又怎么会允许这个孩子活下去呢?哪怕是个痴儿,秦氏也是决不允许有人再来跟她的儿子们争哪怕一文钱。
这孩子是被活活闷死的。
舒忱挖开上面覆着的薄薄一层土时,就看见一张紫涨的小脸,周身连张席子都没有,就这么直接被埋在土里,因为已经有些日子了,那尸体甚至已经有了轻度的腐烂。
那仵作把事情简单的说了,贺峥便感觉到自己怀里搂着的身体颤抖得厉害。他连忙止住仵作的话头:“这些事情烦先生回去再跟县令大人说一遍——届时我会同去。”
仵作亦不是不知人情的人,见了舒忱的模样心中便已了然,自然应允。
而与此同时,沈万金、沈万银连带舒忱的“大舅母”吴楚,也已经赶到了。
沈万金几乎双目赤红,沈万银和吴楚还略好些,却也看得出神情肃穆。
贺峥扶着舒忱前脚刚回家,后脚他们就到了。贺峥把舒忱先安顿好,在房里点了一些安息香——他自己原是不大信这个东西,感觉对自己的效果也不大。但对舒忱就比较管用。
见舒忱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贺峥这才出来招待沈家众人。
此时沈家人还以为此事是一场意外,贺峥将其中弯绕说了,又将舒恰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
待又见过了张嬷嬷,几人已是怒火滔天,恨不得直接杀去舒府撕了秦氏……还有舒县丞。
“当初……当初虽是我们沈家攀附势力才将万珍嫁给舒县丞为妾,当初他也信誓旦旦地说了会好好待他,现在……呵呵现在……”
待又听说了那刚出世的孩子是被活活闷死的,沈家众人已下定决心,这笔账定要让秦氏和舒县丞血债血偿……
宁城是真心不想管这事儿。人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况且这还是自己下属的家务事。
再者他从好歹也是侍郎的庶子,见过比这惊险万分宅斗那也多了去了:这宅斗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谁家内债没点子阴损事儿呢?死个个把人根本不稀罕。
在宁城看来,这内宅之中的事绝无单纯的黑白对错之分,受害的不一定无辜,也许是技不如人呢。
……只是这话他也就在心里想想,若是说出来了大舅哥恐怕要和自己翻个脸……
不管他有多不想管,贺峥求上了门,贺汐也整日在他耳边吹着枕头风,沈家人又击鼓鸣冤把秦氏告上了公堂——也由不得他不管。
民告官是有杀威棒的,不管输赢先打上几板子。因此沈家并没有一上来就状告舒县丞,而是将矛头直指秦氏。
只要告秦氏成了,舒县丞多少得落个治家不严的名儿。到时候再棒打落水狗不迟。
就连舒恰,虽说没有当堂作证,却也偷偷写了证词画了押递了过来。
为了结门好亲事和半抬嫁妆,她也是够拼了。
宁城看了状纸和证词,也不拖延,当下就让人去捉拿秦氏身边的王婆子和她的儿媳妇回来严刑拷打:当时舒县丞还在一旁呢,宁城还象征性地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这要上您府里带人,舒县丞不会介意吧?”
舒县丞还能说什么呢?大人就是这么一问,你同不同意他都是要带人去的。
这事儿,你要说舒忱没有掺和一脚,舒县丞是打死也不信的。
因着秦氏被沈家告上公堂,舒县丞将舒忱叫过来好一阵骂:他出身耕读,极要面子,这回整个舒府的面子都要丢尽了,他每日去衙门总觉得同僚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娘死了,你就要整个舒府为她陪葬是不是?你别忘了,你也是姓舒,舒府的面子落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舒忱木着脸盯着地面,看也不看舒县丞:“败坏舒府名声的不是儿子,也不是舅舅——是谁,父亲心里应该清楚。”
“你!”舒县丞大怒:“你什么意思?难道是我?难道是你母亲?!”
他纵使再不喜欢秦氏,那也是这舒府关起门来得事情。在外面,妻子就是他的另一张脸面,秦氏出了丑,他的脸面也不会光彩。
“她不是我母亲!”舒忱哑着嗓子道:“她杀了我娘,她不是我的母亲!”
舒忱抬起头,直视着舒县丞的眼睛:“父亲,您可以有很多女人,很多妾室——甚至你想的话,你也可以又很多妻子——可是我只有这一个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