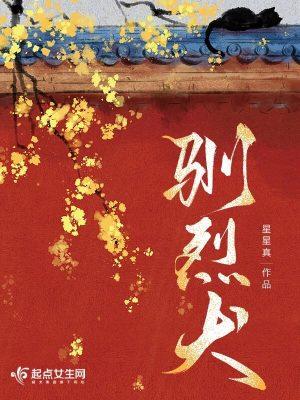江寺刚出殿门,便觉一阵冷风袭来,冷意深入骨髓,他站于阶上,看着底下一众为他请命的人群,神色动容。
最前面的永威候胡须上落满了雪,面容已经冻的有些僵硬,江寺看着这一幕,心底有些难言的滋味。
他缓缓走下去,方正殿的太监护卫一窝蜂上前,将各位大人和公子扶起来。
“陛下有令,北策军骁骑将军江寺破案有功,虽因疏忽酿成大错,但应奸人密谋,防不胜防,故而功过相抵。”
“各位大人,陛下说了,着各位不必久跪,今日盛京落雪,寒意入骨,特命太医院煮了驱寒茶,便随老奴入殿,饮了茶便回去吧。”
永威候被人搀扶着起来,他已有年迈之相,站起身时颤巍巍的,却还是掀开带了冰晶的眼睛,厉目看向江寺。
江寺成人后便不曾同父亲这般对视,如今一看,却恍然觉得父亲脸上多了几分苍老之色。
他衣着单薄,永威候被人扶着前往偏殿时,目光看了一眼他,沉声嘱咐:“多穿件衣服再走,这样的罪受了,便是牛也要大病一场。”
江寺嘴角一扯,笑了笑,同他隔着台阶鞠了一躬。
青毫已经带着狐毛大氅来接人,同江寺一路沿着宫门离开。
方正偏殿,看见底下人散去,孟填才想起自己也要先走一步,否则让人看见不免生疑。
但永威候挥手便能拥支持无数的场面还是让他忌惮。
“永威候府若要尽除,不可徐徐图之,只能一击必杀,彻底铲草除根,才能让人安心。”
他小声喃喃。
候在一边的崔陟将这话全听入耳中,未发一言。
他们都知道,王爷说的是对的。
永威候同江寺,几实在是积威太久,更得陛下器重。
如今便是皇子死,都不能伤及根基分毫。
也是孟填最大的阻碍。
必须除去。
江寺并未御马,从盛京街道上走过,他身后跟着青毫同另外几位心腹。
“今年的雪下的早了。”他伸手接住一片雪花。
青毫知道主子有心事,便道:“未尝不是将军蒙冤,老天都看不过眼了。”
江寺被他一番硬生生又带着点迷信的说辞引出笑意,但眼中酿着锐利冷光。
“事出反常必有妖”,他垂眸,伸出的手掌猛地握住,“北策军不再是一块铁板,这几日忙着查长生观,今日起,便肃清北策军吧。”
以往盛京都是入冬月才下雪的。
以往北策军,也都是忠心于江家,忠心于圣上的。
“将北策军,彻彻底底造成一块铁板”,青毫在他面前恭敬弯腰,便听见江寺,沉稳寂静,带着冷意的声音,“一块,刻着我永威候府,江字的铁板。”
青毫心下一惊,知道将军的意思,忙重重领命。
江寺苍白的手拢了拢衣裳,造大氅遮住他背后斑驳的血迹。
并非是军棍留下,而是在官狱,被监察司处置留下的。
监察司一句“奉命处置江将军”一直在江寺心里回荡,若不是青毫带人赶到,他根本没有机会能出去面圣,戴罪立功。
从方正殿解决一切后走出来时,长生观那位陈道长的警告也在耳边不停重复。
“江世子须知,有时候看到的、说出的,并非是情愿的。人在权力倾轧中,就像漂浮的一叶舟,除了握在自己手中的木桨划开的方向,谁给的路都不能信。”
“就连掌舵的那人的指令,也一样。”
陈方故本不必帮他,可偏偏出门前暗地同他说了这样的话,好像解释一切还有隐情,可又不能多说,半遮半掩,让人心神警惕。
江寺知道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但再查下去,也不会有任何消息了。
他走到候府门口,抬头看了眼永威候府门上的牌匾。
昔年圣上亲自题字,这宅子的定位,建造,都是他一手安排。
登基初时,永威候真是风光无限。
江寺神色有些晦暗。
他推开门,管家早担忧的候在前厅,将他回来,忙带着衣服冲上来,将他包住,忙还着人端着姜茶。
“世子受苦了,那官狱阴冷,哪料到盛京还下了雪,一路受尽风寒,赶紧喝口热的暖暖身子。”
江寺拢紧衣裳,推开热茶,同他摇摇头:“不必了管家,我回院子里歇息歇息,这阵子教我累坏了。”
江寺说话的声音还是平常,看上去好像真的没什么问题,管家被他这般神态晃了晃,觉得有些不对,但又说不上来。
因他要歇息,也不好拦着,便道:“那喝了姜茶便去吧?”
他刚递过去,江寺便一饮而尽,然后阔步踏出去,绕开后院的必经之路,朝着摘星院去了。
翟墨等着他家世子回已经等了数天,一天比一天急,眼看着听闻事情结束,一大早便煮好了热茶,升了院子里的暖气。
等听到大门打开,更是激动的叫了声:“世子爷!”
他声音刚落,立马听见‘嘭’一声。
江寺反手甩上摘星院的大门,‘噗’一声将在前厅喝的一口姜茶吐出来。
翟墨还没走近便闻到浓郁的生姜气息中带着点血腥味。
江寺看着地上一滩血迹,面前景象逐渐模糊,眼前被一片黑暗笼罩,兴许已经知道自己回到了候府,所以便放心得倒下去。
翟墨已经察觉不对,见状神色骇然,忙大叫了一声:“世子!”
“世子,世子,您受伤了?”翟墨跑过去将他扶起,手放在江寺身后感觉一阵湿腻,等他将人放在床上,才看见自己手上已经染了鲜红,他将世子翻过身来。
便见江寺背后,尽是血迹。
江寺在官狱受了酷刑,若不是北策军赶来,他极有可能便死在那里,但从他被带出官狱起,监察司司正,也就是如今宫中的那位执笔太监,带着亲信前来,将对他动刑的几位监察使当众斩首。
似乎是在向江寺证明此事并非他的授意,但仔细品下,更像是杀人灭口。
江寺已经无暇去思考这些,这几日风寒交加,受尽酷刑,已经让他身体病倒,躺在床上没多久,便骤起高热。
永威候说的不错,这样的天寒地冻中跪上三天三夜,便是牛也要病倒。
江寺身体比牛更强壮,也扛不过这几日的阴谋阳谋折腾。
翟墨本为他已经处理好伤口,哪知夜半他热成这样,一时间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
他刚要出门去找府医,结果便见自家公子不省人事间还在念着什么。
翟墨凑近了去听,便听见沈家妹妹的名字。
‘宜亭’二字的音念的缓慢,却格外清楚。
他才像被点醒,忙出院门准备去请沈姑娘。
沈姑娘懂医术,也会用药,定能救他家世子。
沈宜亭尚且不知江寺回府,原她打听今日在方正殿中一切都已解决,永威候同其余大人也都被陛下款待后出宫回府,她担心江寺在外受伤,特意等在回府的路上,想看看他是否无恙。
哪知从早上等到下午,下午等到晚上,始终不见他人影。
最后只好打道回院子。
夜晚时,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院外有一阵小声的吵嚷声,便从床榻上起来,穿好衣裳出门看看。
白苏今夜留在了清风院为小姐守夜,猎场之事后大小姐实在担心她,便教她来守着。
那想到才入夜,世子那边的小厮翟墨便惊慌的跑了过来。
“我家小姐想来已经睡下了,你有何事这样急,不能明日再说么?”
白苏压低声音,歪了歪脑袋,实在无奈。
她不愿扰了小姐安眠,她近几日一直睡不好,今夜好不容易心事放下,早早睡了。
翟墨知道世子隐忍到院中才发作,心中猜想是不愿为外人知道他受伤,便下意识隐瞒,对外也只说:“我家世子有要事请沈姑娘,白苏姑娘,你便通融通融。”
白苏被他这样恳求,态度也犹疑起来,最后还是坚定:“翟墨小哥,你若不急忙,不如等我家小姐醒来后……”
沈宜亭便是这时候出来的,她看翟墨脸上的神情太惊慌急切,便拦下白苏:“怎么了,你这样急,是找我有事?”
翟墨见了她,几乎痛哭流涕,“沈姑娘,小的确实有要事,你不妨同我去一趟摘星院看看我家世子,他,他状况实在是不好。”
沈宜亭脸色一变:“江寺?他回来了?何时回来的?”
她今日都等在路上竟然没等到他,莫非是有意绕开她走的。
沈宜亭也被翟墨带的着急起来,她连忙吩咐:“白苏你在院中守着,若有人来,只咬死了我在休息。”
她随后又看向翟墨:“你且等等,我去收拾东西,马上便同你去。”
她马上进屋收拾大小药品,便同翟墨火急火燎赶向摘星院。
白苏见小姐实在是着急,也知道拦不住,只好奉命在清风院中守着。
沈宜亭去见江寺的一路上,便不住询问翟墨情况,翟墨这才将他家世子何时回来,又是如何吐血,身上如何受的伤,一一道来。
听得沈宜亭指尖都掐进肉里,心里升腾一团野火,逐渐灼烧理智的野草,形成燎原之势。
她知道是谁谋划一切,也明白为何做这些。
她明白,永威候也明白,可江寺不懂。
他像是被卷入漩涡的无辜者,只因为才能过于出众,令人太忌惮,便不得不伪造一副夭折的假象。
她太大意了。
总想着自己能将一切握在手心里,可这世上总有她手伸不到的地方。
长生观如此。
监察司也是如此。
江寺今日受这种罪,沈宜亭心里始终有一团阴霾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