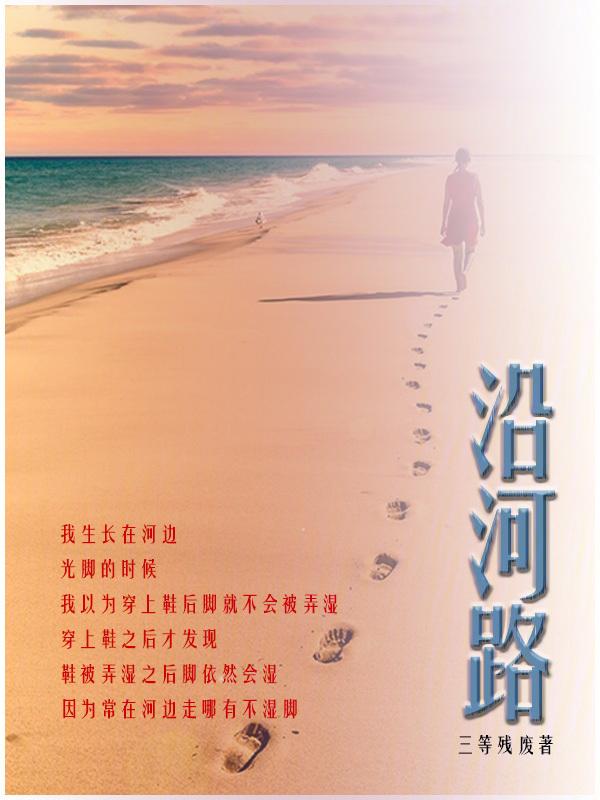离开工业园区,杨泳接着一路西去,但路上的景色却依旧,灰暗的天空、灰黑的浓烟、灰黄的烟囱、昏黄的厂房、枯槁的树木、扬尘的黄土地,如果不是偶尔有几片枯树叶在空中飘荡,很难让人觉得这不是一副末世的油画。
杨泳一路走走停停,不断用相机记录着沿街的荒凉,他心里暗自发出了一声感叹,这世界的颜色都去哪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调转了车头,向北驶去。
不知过了多久,杨泳的眼睛渐渐有了颜色,天空从晦暗变成暗蓝,从灰蓝变成海蓝,再从锃蓝变成湛蓝,最后变成蔚蓝,树木也从枯黄变成翠绿,小草渐渐铺满了路边的泥土,零星还能看到些许红色和黄色。
终于,在一处村落外,杨泳停止了前进,他下车举起相机,拍下了眼前的景色。
行走在阡陌的绿意画卷中,杨泳以那抹绿色为背景,用心灵做底片,定格为蓝天下最生动、最美丽的那帧剪影,是何等的舒畅,何等的醉人心田。在这到处溢满诗意画意的村落,杨泳仿佛自己已经置身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村里的小池塘,还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模样,那未经雕琢的自然之美,在鹅群舞姿的衬托下,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偶有几条小鱼翻出水面,溅起点点水花,荡开层层涟漪,将远山的倒影扭曲成另一幅画卷。乡间的小花,孤独绽放在路边,静静地默守一隅,无论世人的眼光,孤芳自赏,真的是花不醉人,人自醉。被绿色映衬的阡陌,独自漫步的小公鸡,怡然自得地闲庭信步,结伴而行的鸭群,肆意的在田间地头觅食,几只慵懒的黄狗趴在树荫底下,用绯红的舌头舔舐着空气的香甜。
不知不觉,杨泳走到田间,一个老农正顶着斗笠翻看着地里的蔬菜,杨泳走上前去搭讪“老伯,你在干嘛呢?”
老农被杨泳一喊,先是一愣,随后笑着对杨泳说道:“在拔菜呢!”
“我看你在那半天也没动啊!”
“是啊,小伙子,我还在犹豫这菜该不该拔。”老农直起身子,指着地上的菜说道。
“怎么了?”杨泳问道。
“我也不知道这一个窝里为什么会同时长出两种菜,而且这两种菜都是我喜欢吃的,拔了谁我心里都不舍得。可如果不拔,它两又不可能同时长大,所以我就犹豫了。不过当我看到这一片都是红萝卜的时候,我终于有了答案,原来是我自己忘记了,这个位置本来就是种红萝卜的,这颗白菜不过是后来闯入的而已。虽然它也没什么错,可晚了就是晚了,或许这就是命吧!长到这么大才拔,确实有些不舍,不过这也怪我,不在白菜小的时候就把它拔掉,现在反而有些不舍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老农自顾自地述说着,可杨泳却觉得心中莫名触动。
这时,杨泳突然看到老农身后的一块地有些荒芜,明显与这农田中兴兴向荣的景象格格不入,便问道:“老伯,为什么你后面那块地荒着呢?”
老农回头看了看那片地,转头对杨泳说道:“这片地之前是种南瓜的,可是疏于打理,就变成现在这样了。于是我打算把这片地腾出来种白菜,可上面还有些南瓜藤,而且有些藤上还结着小南瓜,这小南瓜没成熟就拔掉我又觉得太可惜了。南瓜藤有什么错,它藤蔓都干枯了,还在耗尽最后一丝生机来供给小南瓜,错的是我,当初明明坚定要种南瓜,现在却又想改种白菜,要改当初也没早点改,等到南瓜都长这么大了,如今怎么舍得拔,所以只好荒着了。”
“哦。”听完老农的讲述,杨泳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怎么这老农说的话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共同点,虽然他说的是种菜,可杨泳总感觉是在说自己。于是杨泳换个话题,指着旁边的一大块菜地问道:“这片菜地都是你家种的吗?”
“那片地啊!那可不是。那块地原来是我家的,不过现在不是我在种了,看着那块地满地生机勃勃,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以前我种的时候天天给地里浇水施肥,但收成总不是很好,所以就给别人了。我以为那块地离开了我会一片荒芜,可万万没想到,它在别人手里依旧能焕发生机,甚至长得更好。果然哪有什么命里唯一、非你不可,一切都不过是高看了自己而已,与其失去后还留恋过往,倒还不如习以为常。”
“老伯,你该不会是受了什么刺激吧!”杨泳听完老农的讲述,不由吃惊地看着对方。
老农此时却有些生气了,说道:“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的,我又没惹你,你怎么说话带刺呢?”
“老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了。”杨泳忙解释道。
“我误会什么了,我告诉你,年轻人,你们这些城里来的人都看不起我们庄稼人,但是我告诉你,有些道理你根本就不懂。你种过地吗?你知道为什么明明杂草长得比庄稼要快,却很难夺得一席之地吗?相反,作为外来户的庄稼却能成为这块地里仅存的唯一,这一切只不过是遵循了种庄稼人的个人意愿而已,就像这白菜一样,它以为它能在这块地里独占鳌头,是因为它足够优秀,却从来不会认为有那么一个种地人时时刻刻都在为它肃清地里的杂草。其实土地从来都没有变过,你看这,种了白菜就叫白菜地,种了萝卜就叫萝卜地,什么都不种那就是一块荒地,但荒地依旧充满生机,有可能还会更加旺盛,所以有些庄稼确实少了点自知之明,要知道你在我地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这个种地人给你的,我要你时,你就是我地里的唯一,我不要你时,你又与那些杂草有什么分别呢?别太高估自己了。”
杨泳听出了老农是在含沙射影地骂自己,但却无言以对,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可是,通过与老农的对话,杨泳觉得这个老农一定不是普通人,于是他谦卑地走到老农身边,递上一根烟说道:“老伯,我只是个大学生,刚路过这里见你的菜地长得挺好的,就好奇问了几句,没想到种地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弄得我也想试试种地了。”
老农斜着眼看了看杨泳,接过烟点燃,随后坐在地头的石头上说道:“你这年轻人也想学种地?种地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哦!记得我刚学种地的时候,以为只要把种子都播撒出去,它们就会生根发芽,长大开花,我就会迎来满满的收获,毕竟这每一颗菜苗都是由一颗小小的种子长大而成的,理论上这是没有错的。可现实就很残酷了,撒在石头上的种子,它只能还是种子,撒在流水中,它只会发芽不会生根,就算撒在土地里,它也需要温暖潮湿的环境才能发芽长大,而且期间还要防止天灾和虫害,否则也是颗粒无收。别以为种子播撒出去的那一刻就是所有的付出,别以为所有的付出都能换来应有的回报,殊不知,目标不对,再努力也是白费劲,经营不善,终究还是白干一场。所有美好的结局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
看着杨泳呆呆得看着自己,老农笑了笑继续说道:“以前我还不懂怎么种地的时候,我总喜欢把肥料一把一把往地里丢,因为我觉得既然庄稼需要营养,那我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它足够的营养,这样它就能更好地回馈给我想要的收成,直到后来被别人发现以后被狠狠地嘲笑了一番,他们说我这样做不仅会浪费肥料,还会造成两种不好的结果,一种是肥料太多了,把庄稼的根烧坏了,让它们活不下去;另外一种就是营养过剩,不会结果,反而白忙活了一场。我当时还想不通到底这是为什么,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做什么事都要适量,爱有度,过则生恨,物极必反呐!”说完,老农丢掉已经抽完的烟头,站起身来。
“老伯这是要去哪?”见老农起身要走,杨泳忙问道。
“我?回家去咯!”说着,老农撇下杨泳,扛着锄头远去,只留下杨泳呆立在原地。
“老伯,我可否能知道您的名讳?”杨泳看着老农离去的背影突然问道。
老农只是远远地摆了摆手,头也没回地吐出四个字“春江老叟。”
“春江老叟?”杨泳心中默念着这四个字,感觉这个名字在哪见过,但又一时想不起来,突然他想到了在万海办公室看到的那副字画,就是那副字画,上面的署名正是“春江老叟”。“你是温……”可话到嘴边,杨泳却发现老农已经消失在田野中,不见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