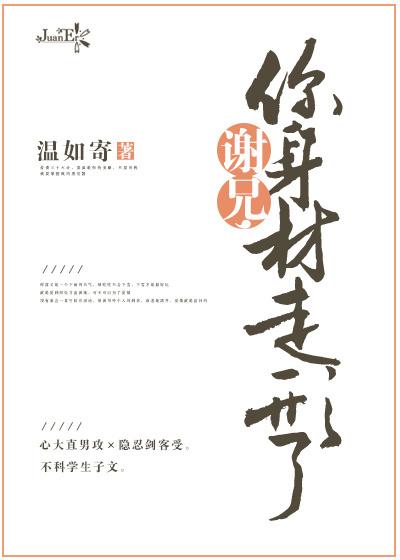90
马车颠簸,他们在去洛京的路上。
一年前, 谢珉行去洛京是去参加师姐的喜宴, 没想到, 一年后再去洛京,却是生死未卜。
谢珉行躺在囚车里,因为身体笨重,实在伸展不开手脚, 有些不安的扭动着,青年怕他这样会压到胎儿,边让他躺在他的怀里,做了个人形靠垫。
裴子浚原本不用跟谢珉行一起坐囚车的, 有裴家这座靠山,他们自然不敢动裴子浚, 可裴七公子却坚持要和他的妻子一起, 他说, “那是我的妻子,肚子里是我的孩子,有半点闪失谁负责?”
他们也只好随他去。
反正关键人物那个大肚子女人跑不了就行了。
午后太阳毒辣,谢珉行口干舌燥, 裴子浚便将牛皮袋中的水, 一口一口喂给他喝,他旁边看押的小弟子不由得看得一愣一愣的, 虽然谢珉行一直坚持那个丑八怪是他要娶的妻子, 可是他们却是三分信七分疑的。
可如果不是夫妻, 又有谁为另一个人做到这份上呢。
到了晚上,一天的颠簸终于结束,他们把谢珉行关进柴房,裴子浚自然也跟着去了。裴子浚私下塞给了两个看押弟子一些钱,又写了个药方,求他们给他抓副药。
保胎药?
有一个弟子家中妻子刚生产,认得这药方,想着抓副药,又不是把人放跑了,就答应了。
裴子浚回到柴房时,看见谢珉行已经清醒了,若有所思在想一些事情,谢珉行蓦然看见青年,不由得一愣,想起白日里青年柔软辗转的唇舌来。
不由得,耳尖泛了红。
他觉得自己真是荒唐,自己这副模样还想些色、欲熏心的事情,真是不要脸面了?
于是,别过脸去,不看裴子浚。
裴子浚看他这副模样,想着,谢兄莫不是恼了?他翻来覆去思索了个遍,忽然开了心窍,莫不是因为白日里的那种事?
他想,虽然是情势所逼,可是他何尝不欲而不得?这倒是真应了唐不弃骂他的,他,裴子浚,是个举止轻浮的登徒浪子。
他觉得自己应该向谢珉行道个歉。
“谢兄,白日唐突你,我实在……”
谢珉行好不容易才掐下去的火苗,却被裴子浚这样堂而皇之的重新提出来,又羞又恼,“不介意!”
裴子浚被吓了一跳,有些惊愕的看着谢珉行,他没有想到谢珉行反应这么大,想来也是,谢兄心里自有爱慕的人,他又不是那个人,他自然心里不舒服。
可是一想到那个谢兄的心上人,他就更不是滋味,谢珉行身陷囹圄,受尽苦难,可是那人,却从未露面。
对于那个人的身份,他不是全然未觉,却一直不敢去正视。
他当做珍宝的人,却被别人这样弃之敝履。
他恼怒至极,脱口而出,“你的心上人到底……”可是话到嘴边,又害怕真的从谢兄口中听到了那个人的名字,改口道,“也是阿衣的父亲吗?”
谢珉行楞了一下,他不知道为什么裴子浚忽然会问这件事,可是他这样的丑态都已经暴露在他面前了,又有什么可隐瞒的。
于是点点头。
裴子浚得到了证实,小心翼翼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谢珉行望着青年,青年的眼里似乎有点点星光,将他整个人都装进了瞳孔里,于是由衷道,“他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他心中更加恼,事到如今他还在维护那个人,却听得谢珉行又道,“一切都是我甘愿。”
所有的怒意,都被这一句“我甘愿”浇得透心凉,一拳打在软棉花上,他无处发泄,只好默默苦笑了一下。
爱恨嗔痴,不过始于一句“我甘愿”。
也终于一句“我甘愿”。
91
两个人各怀心事,谁也没有睡安稳。
半夜里柴房门外又传了喧嚣声,似乎起了争执,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却看见门外灵巧钻进来一个小崽子,看见谢珉行的大腿就抱了上去,呜呜呜哭个不停。
谢珉行:……
这孩子怎么那么爱抱大腿?
几位看守的弟子看见了无可奈何,这可是唐家金贵的小孙子,和病女人呆在一起,沾染了什么病怎么办?
可是唐不弃跟牛皮糖一样,怎么也没办法从谢珉行身上剥下来,他们打不得,骂不得,只能大眼瞪小眼。
最后还是裴七公子说,“让他待在这里吧,我会照顾他的。”
一场风波终于平静了。
谢珉行看向看着哭得抽抽搭搭的丢丢,好笑,“怎么?高床软枕不睡,要来睡柴房?”
“我只想跟谢哥哥呆在一起。”丢丢止住眼泪,认真道。
他遭逢变故,被谢珉行从潇湘里带出来,他突然间有了自己的亲人,可是,能让信任的人,却只有在他母亲火化时那个用双手蒙着他眼睛的谢哥哥。
谢珉行虽然沉默,却也看得出这小孩有心事,可是小孩儿不说,他也不想逼迫小孩儿。那时候唐不弃离家出走,来投奔他时,他就觉得不对劲,丢丢不是那种娇宠长大的任性的孩子,离家出走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事情,导致他在唐家待不下去了。
可是他一个小孩儿,又是唐丰的独子,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呢?
他想不明白,索性把小孩儿抱在怀里,沉沉睡去。
在陷入黑甜的梦境之中之前,他忽然想起来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白日里裴子浚说他有一个未婚妻的时候,没有人惊讶,显然他们都是知道的,说明未婚妻这个人真的存在。
他就要成亲了。
谢珉行看着裴子浚的背影,毫无波澜的想。
92
蓟州和洛京本来不远,他们这样一群人浩浩汤汤,却有些耽误行程。
这样一来,南郡和其他英豪都陆续到达洛京,他们却还在路上,这让谢珉行很担心一个事——算算日子,也差不多就是这几天了。
这些日子来谢珉行的胎动越来越明显,那个肚子里的小怪物已经亟不可待的想要出来了。
裴子浚刚给谢珉行把完了脉,眉头深锁。
实在太不是时候了。
现在路途颠簸,困难重重,又马上要对簿公堂,山雨欲来。
阿衣呀阿衣,你真是个小讨债鬼。
裴子浚这样想着,却又开始想那个金蝉脱壳之计,谢珉行当然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对裴子浚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我这样的怪物,也想请你帮我保存最后的尊严,我不想……再玷污师门清誉了。”
他顿了顿,“还有一件事,就在半年以前,宋师叔说我偷拿了藏书楼里一样东西,才会把我关……总之,如果真有那样东西,如果我没有机会寻回,也请你帮我继续追查。”
裴子浚一一点头,却越发难过。
他的谢兄啊,总是想着怎么寻回师姐,怎么维护师门,就算是他那个狼心狗肺的心上人,在他口中也成了个极好的人———可是,他为什么不多想想自己?
这些天丢丢被唐家的人领回去,又跑过来,如此往复了好几次,终于消停了,谁知道,就在抵达洛京城的第一个晚上,丢丢又溜出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要给裴谢两人看。
这一回,丢丢说,“哥哥,有一件事我放在心里好久了,一直不敢说。”
他几乎要哭出来了,“可是我阿妈不能这么白白死了。”
谢珉行安慰地拍了拍小孩的背,丢丢吸了下鼻子,继续说——
“我跟你们说过,阿妈在死前曾经见过一个戴面具的叔叔吧,就在不久之前,我又重新看见了他。”